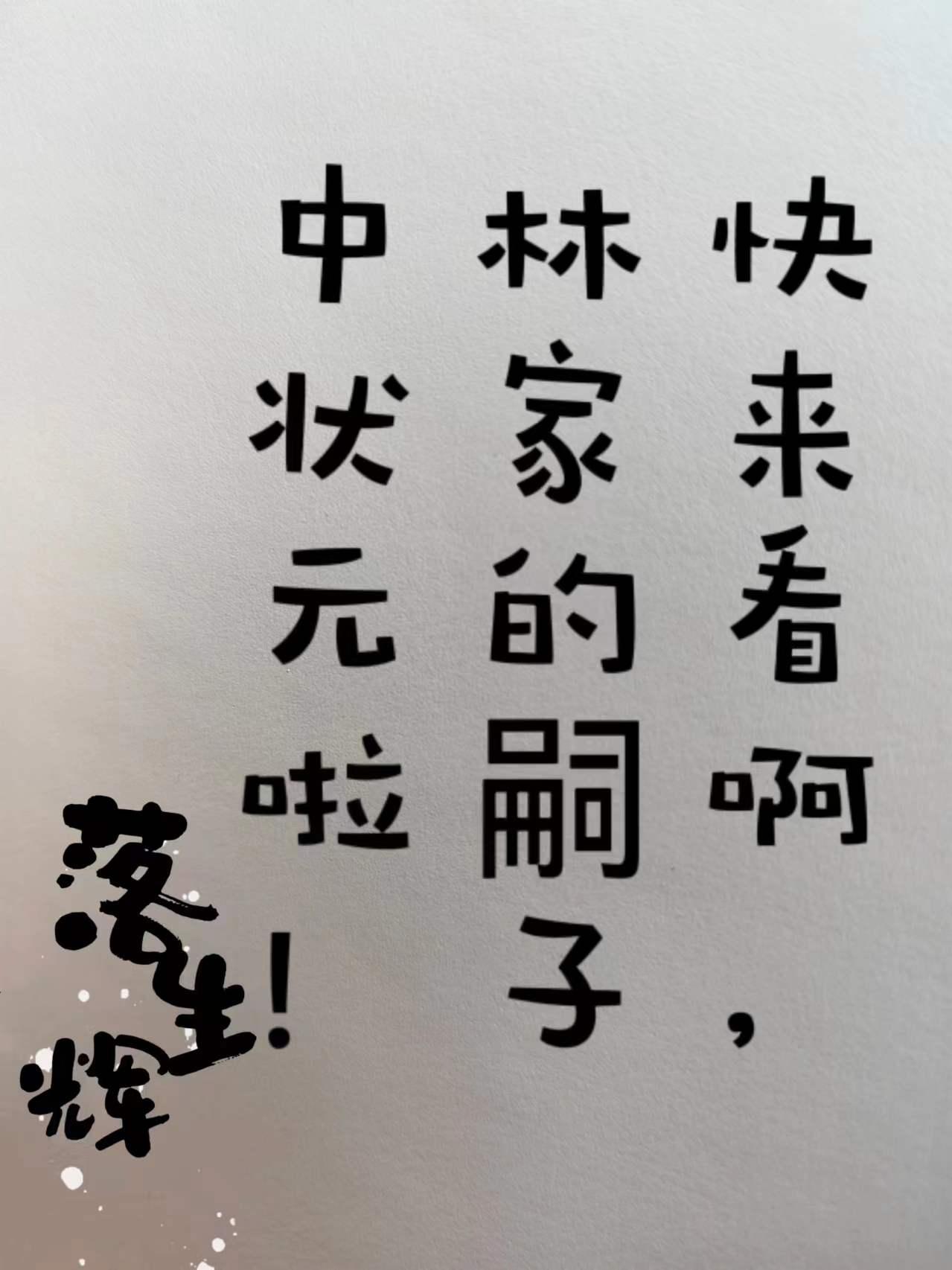笔趣小说>江湖第一女刺客 > 第217章(第1页)
第217章(第1页)
刀刃映着他的容貌,如幻境中开放的玉兰花,破碎而不真实。
然而眼前的一切又何尝不是。
美人执刀。明明从小就在练习“稳”这一个字,甚至为此吃了不少寻常人根本想象不到的苦,可现在拿着刀的那只手却还是在轻微的颤抖,如同漂浮在半空中的蜜蜂蜂翼一般,轻轻一压就会垮下。
手背因为用力而青筋浮现,说不紧张的都是假的——即使在秋月白最难熬的时候都没有想过现在他要去做的这件事,以前是想不到,后来是不敢,再到最后几乎已经要忘记还有这个可能了。
而今天,他却出于种种理由将这一件事重新拾起来,像光脚踩在河滩上寻找着当年扎伤自己的一颗钉子……已经不知道还有没有找到的可能,却还是要努力去做。
即使寻找的过程中可能会想起当年被扎伤的痛,即使可能会被再扎伤一次……也还是不得不去做。
冷汗打湿背后,秋月白仍然在面无表情的寻找着时玄兰的踪迹,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到处都没有,时玄兰难道是在躲吗?他居然也会躲着自己??
——亦或者,故弄玄虚?
秋月白调整着呼吸,无声无息的从院子里退了出来,饮黄泉已经不见了,应当是已经被主人带走。他浑身肌肉紧绷,在脑海里思索着人到底会在哪。
直到一个转身,余光瞥见一侧角落里盛放的腊梅——其上多了一朵本不该属于这里的花。
一朵应盛放在坟冢之前的花。
秋月白用刀尖将其挑下,捻在手心,呼吸都放轻了。
随后,立马转身离去。
-
深冬,大雪,花海如同被棉被盖住,白茫茫的一片。
有侥幸躲过大雪摧残的花朵从夹缝中冒出,与秋月白在院子里的梅花树上看见的一模一样。
他依照着记忆沿着路往花海深处走去,脚踩在雪地之上、一深一浅的发出几乎听不见的沙沙声,这样短的一条路偏偏能给人一种要走一辈子才能到头的感觉——太静、太孤寂了,时间过去得又快又慢。
或许只有一个人走的路都是如此。他想。
再往前走了一会儿,终于,秋月白遥遥看见了那被雪压着的孤坟,它就那样沉默的坐在那里,披着雪,迎着风,墓碑好似利刃一般的立在它的前面,直挺挺的。
秋月白与“明月夜之墓”擦肩而过。
而后顿住,垂着眼用刀将脚边的积雪刨开,使下面冷硬的石板暴露在视线之下。
他回想着上一次与时玄兰一起来时那人打开机关的场景,有样学样的推敲着,不一会儿就听见“轰隆”一声——机关打开了。
从地下吹出的冷气却让人又出了汗,秋月白的手握得更紧,丝毫不迟疑地走了进去,拿起一盏旁边的灯照着明,朝着地底深处看去。
他的步子很大,也很快,每一步都是在确认自己的决心,每一步都踩在冰冷的石板之上,一点声音都没有。
也不知走了多久,终于见前面有了一点光亮。
秋月白呼吸放轻,本来就无声的脚步也更加轻巧,他迈入那片光亮,迅速进了那片空间,华丽明亮的高楼立刻出现在眼前,周围的傀儡都停止了活动,一排排一列列的站在两边,笔直又冷峻,眼睛盯着秋月白进来的方向。
傀儡、高楼、注视的目光……这是一个乍一下看上去会觉得有些恐怖的场景,加上内心的紧张,即使沉着如秋月白,也不免心中咯噔一跳。
他环顾四周未见人影,内心已经有些忐忑,就在这时,听见楼上遥遥传来人声,温和无比。
“你的刀不稳。”
那一声中带着审视,判断与批评,又带着一些长辈对晚辈的爱惜,声音飘忽无比。
秋月白猛然抬头,终于见到了站在最高处的时玄兰!!
他一身锦衣华服,背着手看向楼下,脸上带着熟悉的木头鬼脸面具,箫、扇子、刀一样不少的带在身上,目光很是阴森。
就这样对视时,秋月白下意识想退后一步,又被他控制住。
时玄兰观察敏锐,自然不可能错过这一点,他察觉到了自己这个孩子内心深处的恐惧与紧张,并且因为这一点愉悦的莞尔一笑:“我还以为你过来就是准备好了,没想到只是个半吊子么?”
他足尖轻点,踩着瓦与檐飘然从楼上跃下,平稳得头发丝都未曾乱过一根。
时玄兰的目光漫不经心扫过面前人手中的刀,似笑非笑道:“……你这个状态,实在不适合杀人。”
秋月白嘴唇颤抖,到了这个时候,他反而更加不知道说什么好,二人的关系太过复杂,十余年的相处使他不可能如其他人在面对仇人那样严厉的说出“纳命来”这一类的话,也绝不可能保持几乎一成不变的淡定来面对这一件事——情绪是一件很复杂的东西,许多人一辈子都未曾琢磨透。
可是另一方面上,他确实无比的恨面前的这个人,这已经是一件隐藏不住的事了。
“你……”秋月白冷冷的盯着他:“死到临头,只说些这个么?”
这句话莫名的让时玄兰笑了出来:“阿月,以前你并不是一个会见大话的人啊。”
秋月白却于沉默时猛然拔刀!!
刀带着劲风劈来,时玄兰不慌不忙握着紫竹箫,只是轻轻一转便坐到了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凌厉的刀非但不能劈断那根脆弱的木头,反而还被抵住。
这让秋月白不由得露出一个惊讶的表情。
时玄兰慢慢说:“怎么?你觉得我内力已经没有了、便可以对我随意砍杀?阿月,我在你的心中有这么脆弱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