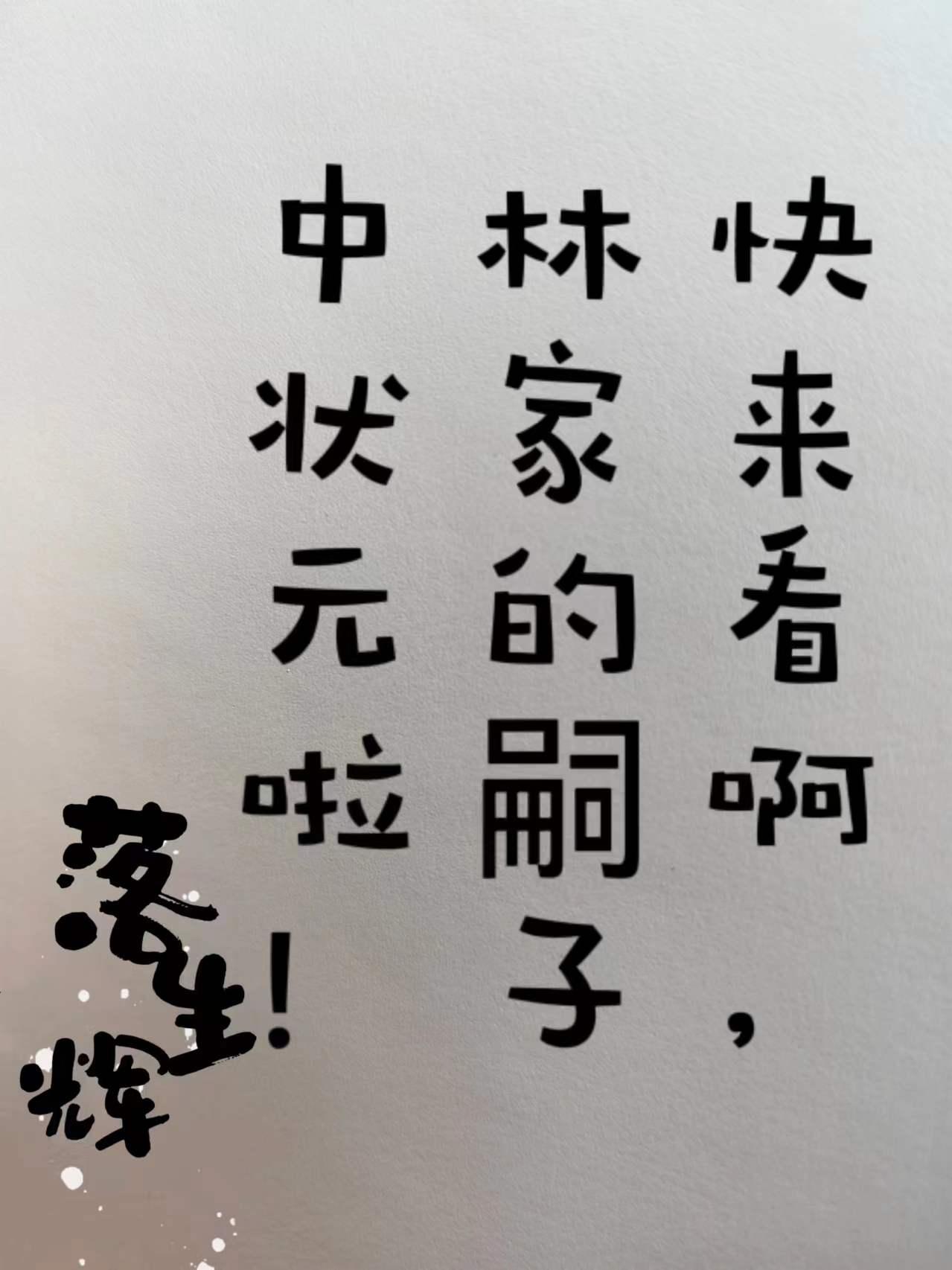笔趣小说>你走丢了怎么办报警就好抱紧就好 > 第53章(第1页)
第53章(第1页)
贺白沉默着没答话。
蒋萍见状,忽然收了笑容。
“为什么今天回来这么晚?”
尽管客厅灯光很足,但蒋萍的表情依旧看起来有些阴森诡异。
“”
“我问了你们科室的小吴,她说你今天正常下班,你干嘛去了?是不是有事瞒着我?是不是刘虎来找到你了?还是吴天良放出来了?还是还是你去找陈建芸她儿子了?!你又找他!你又要去找他!!你是不是要把我逼死才肯罢休?贺白!贺白!!”
蒋萍像忽然被开了什么开关,声音一步一层的越来越响,她拽着贺白的衣袖,疯狂的撕扯摇晃。
蒋萍的动静惊醒了里屋的贺薇,听到母亲的嘶吼,贺薇顾不上刚被从梦中拽出来的头痛,路都走不稳,跌跌撞撞的冲了出去。
她搂住蒋萍的腰,把蒋萍从贺白身上撕下来:“妈!妈!怎么了这是!贺白你又干什么了你?!”
贺白疲惫的扶额,低声说:“妈,别闹了。”
“闹?你以为我疯了是不是?你们都以为我疯了是不是?”
蒋萍在贺薇怀里颤抖着,哭了笑,笑了又哭,她深吸了一口气,嘴里喃喃道:“明早我陪你去辞职,不要去上班,不要出家门,外面太危险,你们两个就跟在我身边,哪儿也不许去,别怕孩子爸爸走了还有我,我不能让这个家垮了不能垮了不能再垮了”
苍老母亲干瘦如柴的手慢慢松开了贺白的衣袖,贺薇赶紧扶住了蒋萍不让她摔倒。
贺白抬了抬下巴示意贺薇,让她把蒋萍扶回房子里去,自己径直走到贺振华灵台前,擦了擦母亲刚碰撒的香灰。
他站在父亲面前默了默,从木桌的抽屉里拿出了两瓶药,去了蒋萍的卧室。
“去烧点热水。”贺白手里捏着药瓶,对屋里的贺薇说。
那时蒋萍已经被贺薇照顾躺下了,贺白无声的坐在蒋萍床边,按照药瓶上医生手写的医嘱,把几粒小片倒进了药瓶盖子里。
“小白啊”蒋萍躺床上小声的唤。
“嗯。”
“你是不是找到他了?”
贺白手下一停,抬眼看向蒋萍的双眼:“对不起,妈。”
“”
“我从来没有弄丢过他。”
前夕
安安进仓快一周了,为了不让他一个人在里面太无聊,安安妈妈给儿子带了游戏机和手机进去。
小孩儿没事儿就给方黎发消息,无聊的问候,有趣的视频,新奇的图片,什么都发,有时还邀请方黎跟他在网上打游戏。
尽管孩子的兴趣点在方黎看来可能很幼稚,但他还是尽自己所能,只要有精力就多陪陪安安。
毕竟只有十岁的孩子,要独自呆在那个又闷又小的密闭空间里,被病痛折磨被药物摧残,父母亲人只能远远隔着一块儿玻璃看着,摸不到也抱不着的。
再加上安安又懂事,进仓后难受了从不跟父母说,只跟来的医生护士汇报,偶尔再找方黎发发牢骚。
方黎就像是个能与他同进退的同窗,成了那个离他最近的人。
刚开始的几天,安安基本一整天都会粘着方黎。
但这一阵方黎明显觉着安安话少了,有时他主动去逗这小孩儿,那头甚至好几个小时都杳无音信。
方黎心里有点毛,想去看看安安。
蒋沐凡听闻方黎的担心后,也有点放不下这位小病友,他去取得了任明的允许,找了个风和日丽的一天,把方黎推去了隔壁楼上。
隔离楼也是血液科的住院楼,只有四层高,基本装的都是层流室。
住的要么是靠无菌环境吊着一条命,活不过天的重症,要么就是安安这种打算进行骨髓移植的。
去看安安那天,两人一进病区,就被那处处是绝望的死气牢牢裹起。
医院将这一整栋楼从中一分为二,隔出了两个板块,一半是层流仓,一半是正常的家属的陪床和办公区。
层流仓之间是相通的,有医护人员的专用通道,医生进行全身消毒换上防护服之后,从通道过去可以一间一间的查房,与普通病房无差。
家属只能在仓外,与病人隔着一块儿密封玻璃,每日像是观察玻璃盒子内的小白鼠一样陪着自己的亲人,说话交流要么靠手机,要么就像探监似的用病房里安装的无线电话。
这栋楼里的空气可以用寂静来形容,不论病人还是家属,他们小心翼翼地醒着小心翼翼地睡着,生怕一个不小心惊动了站在门口的死神。
方黎和蒋沐凡到的时候,仓外就稳稳一个人,正趴在家属床上画画。
“稳稳。”蒋沐凡笑着打了声招呼。
稳稳闻声回身看,一眼认出了蒋沐凡,却没有认出方黎,他看着轮椅上的方黎愣了片刻,奶声奶气的叫了声:“凡凡哥哥。”
“不认识我了?稳稳?”方黎笑问。
这时安安妈妈从门外进来,一只手拿着沓报告单,一只手捏着团餐巾纸,鼻头泛红,眼角湿润,明显是刚哭完的模样。
见有客人来,安安妈有些猝不及防,硬扯着嘴对方黎和蒋沐凡笑:“方老师,你们怎么来了。”
“这两天不见安安找我,有点担心就想来看看,刘姐,安安最近怎么样?还没做移植吗?”
“一时半会儿还做不了。”安安妈难过的摇摇头,“这前期的准备工作跟我们想的不一样,太痛苦也太复杂,安安还小,一时半会撑不下来。”
蒋沐凡走到玻璃面前看着那个躺在床上的小人儿,有些震惊的问:“层流室也会出现感染吗?这不是绝对无菌环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