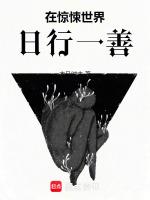笔趣小说>这个杀手有点黏免费阅读 > 第6章(第1页)
第6章(第1页)
生气。
陆九宴丢了陆家的商契,又遇到这种事,一时间没心情回府,便沿街找了家茶楼,在二楼靠窗的位置颓然坐下了。
隔壁围炉煮酒的一群人里,有两个男人瞥见陆九宴,相视一笑后,端起酒壶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
其中一人弯着腰,眯起眼,脸上挂着不怀好意的笑,他凑近陆九宴,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阴阳怪气地笑道:“这不是陆少爷吗,怎么今儿没缠着州主,反倒一个人坐在这儿喝凉水。”
另一个人凑过来,撇着嘴嘲笑道:“陆家如今不似从前了,怕是陆少爷更不受州主待见了吧?毕竟现在宋家才是沧州首富。”
往常都是宋陆两家争这个沧州首富之位,宋家因故未能赴约柳府宴,阴差阳错逃过一劫,手下商铺没有受到什么损失。而陆家差点折了一根独苗,为了陆九宴的事疏忽了生意上的问题,被同行使了绊子,折损不少商铺。
商场如战场,这本是稀松平常的事,可是从这两人嘴里尖酸刻薄地吐出来,就听着格外刺耳。
陆九宴平日里能说会道,常常将他们抵得哑口无言,如今他们听说他伤了嗓子,说不得话,就更加狂妄了。
陆九宴厌恶地睨了两人一眼,朝慕叶使了个眼色。
慕叶早就等不及了,得到命令立马挽起袖子,气势汹汹地上前,飞起一脚,狠狠把这两踹倒。
隔壁其他几人见状,纷纷放下手中的杯子,其中有两人甚至撸起袖子准备抄家伙,被旁边人眼疾手快地按住了。
“这陆家少爷好歹是州主身边的一条狗,打狗还得看主人呢,切勿莽撞。”
那两人才重新坐回来,声调丝毫没有遮掩,一脸的张狂,“也是,狗仗人势的东西,难得与他计较。”
话音刚落,一个茶杯猛地砸在了他们面前,瞬间碎裂,碎片飞溅。
陆九宴怒不可遏,低吼道:“你再说一遍咳咳……再说一遍试试!”
那群人见状,先是一愣,随即爆发出一阵放肆的大笑,用逗弄的语气道:“哟,今儿哑巴狗要咬人了。”
陆九宴气得满脸通红,额头上的青筋突突直跳,他拍案而起,目光四下找寻趁手的家伙事。
“少爷,冷静,冷静。”慕叶紧紧抱住陆九宴的身体,生怕他大伤初愈又伤了自己。
少爷从前根本不在乎这些闲言碎语,更没有把这些狺狺狂吠的人放在眼里,可是如今,少爷为什么这么生气?
他正思索间,陆九宴已经挣脱他的阻拦,飞起一脚将隔壁桌子踹翻了,桌上的酒菜洒落一地。那群人也傻了眼,愣了一下,随即一个个张牙舞爪地扑过来,眼看着就要打成一片。
一阵整齐有素的脚步声从楼下传来,很快便近在耳畔。
州府的府卫火速将几人拉开,以寻衅滋事罪将他们押入了州府衙门。
州府衙门紧靠着州府,负责审案的大人原本是右府官棠舟,但因棠、陆两家是姻亲,为了避嫌换成了左府官赵无笛。
“……大人明鉴!草民只是与陆公子开了几句玩笑,他便命人将我与周兄打成这副模样!”
堂上,一边是一身无尘、身姿挺拔的陆九宴,神色冷峻,另一边是几个鼻青脸肿、狼狈不堪的青年,正哭丧着脸,不停地诉苦。
赵无笛沉着脸,目光严厉地问:“陆九宴,可有此事?”
陆九宴道:“我确实打了他。”
慕叶急忙上前一步,道:“大人,是他们先对我家公子出言不逊!”
府卫呈上纸笔,将那些出言不逊的话一一记录在册,赵无笛扫了一眼,眉头紧皱,沉声道:“确实无礼,州主之事岂容尔等造谣!来人,将这几人拖下去,杖责三十。”
其中一位名叫周松柏的男子听到这个判决,不服气地反驳道:“我们故而有错在先,可他陆九宴指使家仆打伤我们,难道就没罪?”
慕叶挺起胸膛,大声道:“大人,人是我打的,此事与我家少爷无关,草民甘愿领罪。”
赵无笛道:“陆家家仆出手伤人,但念在事出有因,陆家要赔偿受害人所有损失,外加杖责二十。”
周松柏不甘心道:“大人,人虽然不是陆九宴打的,可他才是主谋,难道他不就受罚吗?”
“陆九宴,指使家仆出手伤人,杖责二十。”赵无笛取出发签,重重地掷在地上,“即刻行刑!”
行刑处,以周松柏为首的几个城中纨绔接连受了杖刑,却赖着不肯离开,一个个斜倚在墙边,嘴角挂着幸灾乐祸的笑,准备欣赏陆九宴被杖责。
他们几个身强力壮,挨了打无非是躺个几日,陆九宴大伤初愈,可不一定受得了这二十杖。
周松柏冷笑。他暗中买通了行刑的府卫,绝不让陆九宴站着回去。
慕叶受完二十杖,却不起身,艰难地抬起头,担忧地看着陆九宴道:“少爷,你的杖刑,我一起受了。”
陆九宴还没开口,周松柏等人便叫嚷起来,手舞足蹈地说:“谁允许你替他受刑?赶紧起来,否则便叫赵大人来评评理。”
“赵大人来不了,我可做得了这个主?”
说话之人,是叶挽的心腹女官,宋娆。
只见她款步而来,神色威严,那带刀的眸子犹如寒星般,冷冷地从几位纨绔子弟身上扫过,目光所到之处,让人不寒而栗。
那几位纨绔子弟在这凌厉的注视下,不自觉地瑟缩了一下,仿佛被这目光生生冻住了动作。
她的出现几乎代表着州主的意思,府卫纷纷恭敬地弯腰行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