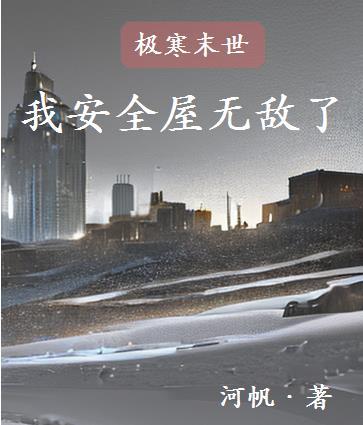笔趣小说>落第县令 > 第5章(第1页)
第5章(第1页)
“白瞎子,长点心,穷乡僻壤长出的人,到底刁蛮。”许桥说着,从怀中掏出一个瓷瓶,丢给白全晨,白全晨吃了瘪,连反驳的话都忘了说,呲个牙处理伤口。
白无秋将一切看在眼里,心中对苦崖村的期望又降低几分,一想到自己又恨又爱的人长在这种坏境,难免担忧几分。
他走到牧童面前,秀挺的身姿罩住地上的人,牧童匆匆瞄了眼,只见这个人的气质不同,相较于刚才两人,多了分贵气,举手抬足间都透露着优雅。他咽了口唾沫,只觉得惹了麻烦,心如擂鼓般跳动。
白无秋面容平淡,蹲下身与牧童平视道:“你是苦崖村的么,你伤了我的朋友,劳烦你带路找个大夫,不用你出钱。”
牧童瞪大了双眼,一张俊美的脸措不及防在他眼前放大,那人一双桃花眼,羽睫纤长,翘挺的鼻梁上点缀着一颗淡红的小痣,薄唇微抿,透出淡淡的粉。
不知怎的,牧童忽地红了脸,若不是此人开口声音低沉,他都要以为是女扮男装的仙子,他压下那股紧张劲儿,有些结巴道:“是……是,我这就带你们去。”
白全晨靠在许桥背后,举着绷带缠得乱七八糟的手,瞪着牧童,气不打一处来,白无秋朝他挑眉,什么都没说,又像什么都说了,留他一人风中凌乱。
许桥也用戏谑的眼神看他,在他身旁道:“这小孩挺会看碟下菜。”
白全晨不再理会,窝心地将许桥绑的蝴蝶结拆开重新绑好,许桥咋舌,怎么看那一团都是个疙瘩。
牧童也识趣的,不敢并排走在许桥白全晨身旁,眼珠子提溜一圈,决定贴着看起来最好说话的白无秋,白无秋没有揭穿他的小心思,只在牧童蹭脏他的衣角时,不动声色与他拉开几寸距离。
白无秋见牧童不似寻常人家小孩,甚是狡黠,又见他褂子上沾了些许黄泥,而后山又没有这样的土质,心中猜疑起来,不禁开口问道:“小孩,我见你方才慌慌张张,是有什么事儿吗?”
牧童一脸颓唐,正担忧着丢了牛又得罪了人,回家肯定要挨打,见白无秋问他原由,天真以为这位贵人不计较刚才的事了,于是装出可怜兮兮样子,哭丧哀嚎道:“这位大人,您是有所不知,我们村子有个疯子到处打人,专门欺负老人和我这样的小孩儿,我刚才路过他家的田地,多看了眼,他就抢了我的黄牛,还把我揍了一顿。我也是太害怕了,才不小心咬了您的朋友。”
说罢,偷偷瞟了白全晨一眼,白全晨不吃他那一套,恶狠狠朝他比了个拳头,吓得牧童就要朝白无秋怀里钻。
白无秋一边感叹于他的厚脸皮,一边按住他的头,把看戏的许桥叫到跟前,牧童才肯消停下来。
“想必那疯子是个恶人,你们可曾报官?”白无秋又问。
牧童这次显得矜持多了,摆头道:“报过了,只关了几日便放出来了,官老爷说他家还有个老爹子,让他先尽孝。”
许桥抽了嘴角,这牧童张口就来,说的话也漏洞百出,但也没有揭露,他家公子这样问,无非是想套些话,并非真的对什么疯子感兴趣。
不过他也好奇,白无秋放着繁华的锦城不待,非要当个荒州刺史,还不远千里跑到岭川的一个小小村庄来,那人当真有如此魄力,让白无秋心甘情愿念了六年。
“明兄,前方有村落,看来是到目的地了。”
‘明兄’是白无秋为自己起的假名,许桥和白全景分别叫二乔、三水。
白无秋点头,牧童跟着高声道:“对的,前面就是我们村子了,这位明大人,我听你们说目的地,是不是要来我们村子游玩,您要是不嫌弃可以来我家做客。”
许桥冷哼一声,掠过他的目光道:”你说错了,我们是来探望人的。”
牧童挠头,实在不解,苦崖村这穷乡僻壤,谁会和这样贵气的人攀上关系,不由得把心里话说出来:“我们这儿穷山穷水,几年也没出个几个出息人,你们上这儿找人怕不是找错地方了。”
“不会错的,就是你们村,我问你,你们村有没有一户姓章的人家。”白无秋倏地问道,眸光如潭水深沉。
牧童愣住了,以为是自己耳朵出了问题,整个苦崖村,除了章景那一家子,还会有谁姓章。
白全晨趁他发愣的空隙,抓住他的胳膊,凶神恶煞道:“实话实说,别装糊涂。”
白无秋用扇子敲了白全晨的头,桃花眼笑盈盈的,盯着牧童,等他答复。牧童知道他们不好搪塞,只好一五一十将事情交待了,顺便添油加醋将章景的恶行复述了个遍。
本以为这位‘明大人’会以章景为耻,却见白无秋如同拨开云雾见青天,连眸子都明亮三分,一旁的许桥、白全景僵在了原地,不相信牧童口中的‘疯子’就是自家公子要找的人。
再说章景,吓走了牧童后,牵着老黄牛回到村东头,把牛拴在牧童家门口的桑树,村民见了以为他馋涎牧童家的家畜,都把自家养的鸡鸭关好了,锁住院门,只敢缩在一起嚼舌根。
章景不在乎那群人说了什么,随手摘根草,放在在嘴里咀嚼,享受着春日的阳光抚在脸上,不知不觉,竟是走到了溪边。
溪边的柳树下,三三两两的妇女聚集在一起,见章景来了,一个个见瘟神般丢下木盆跑了,章景杨眉,觉得终于做了一回正确事情,只要没脸没皮,生活都顺畅不少。
他坐在溪水边,看着水中倒影,忽然看见,水中的那个章景,变了不少,腮边长了浅草般的胡须,头发和玉米须一样杂乱,眼睛下面挂着圈淡青,当然,这相较于去年冬月,还算不错得了,至少他的长了几两肉,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父亲超出了余施的预言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