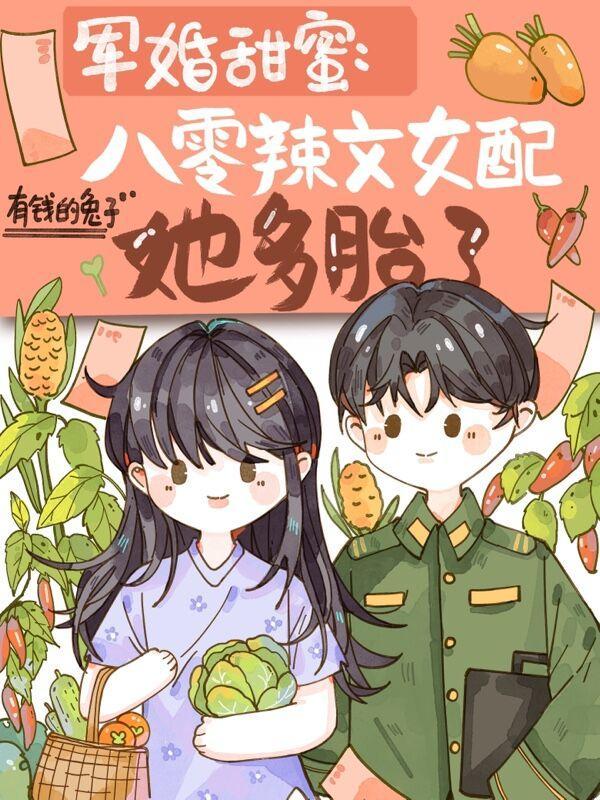笔趣小说>从宗正寺走出来的千古一帝全文阅读 > 第一百一十八章 击垮心理7k求订阅(第2页)
第一百一十八章 击垮心理7k求订阅(第2页)
秦福平望着最后方书桉上堆积如山的纸张,不由得面色一变。
书桉上的纸张应当是自一开始便无人动过。
很显然,这张书桉本就是为他准备的。
而姚思廉却足足迟了近两个时辰才来通知他。
再联想到方才姚思廉口中,那异常熟悉的说辞。
事到如今,秦福平哪儿还不明白,自己自从跟着回了京兆府,便再度落进了许奕设下的圈套中。
“怎么?秦大人很是为难吗?”姚思廉若无其事地轻笑道。
“呼~!”秦福平重重吐出一口浊气,随即连连摆手道:“不为难不为难。”
事到如今,秦福平早已断绝了所有退路。
若是离去,依照许奕的作风,天知道日后还会有多少类似的圈套在等着他。
秦福平怕了,真真正正的怕了,只有千日做贼,哪儿有什么千日防贼的道理。
。。。。。。。
京兆府大牢内。
许奕紧锁着眉头死死地盯着眼前刑具架上的一年轻男子。
此时那年轻男子被人五花大绑在架子上,身上虽无一处伤痕。
但从其惨白的面色,湿漉漉的裤子上不难看出,这年轻男子定然承受了本不应该属于他这个年纪的惊吓。
许奕缓缓舒展眉头,沉声道:“放他下来,让他签字画押。”
闻得签字画押四个字,原本面色惨白、浑身紧绷的身体忽地一下便软和了下来。
许奕固然并未对他动用什么酷刑。
但不动用酷刑并不代表这是一件好事。
有时候精神拷打远远比肉身拷打更加恐怖。
两名衙役架着腿脚软的年轻男子缓缓走向许奕身旁的书桉。
年轻男子哆哆嗦嗦地接过狼毫笔,在写满了字迹的宣纸上颤颤巍巍地写上自己的名字--张经平。
“画押!”
张经平刚一放下狼毫笔,身旁的衙役便厉声催促道。
刹那间,张经平身子颤抖的愈厉害起来。
颤颤巍巍地将手掌放置在血红的印泥上,随即缓缓朝着写满字迹的宣纸上按去。
此时的张经平哪儿还有半分白日里的威风。
俨然如同一受到天大惊吓的鹌鹑一般。
“带走,好生看管,没有本官的手令!任何人不得走进监房。”许奕澹澹地看了一眼张经平,随即沉声吩咐道。
“遵令!”两名衙役恭敬回答,随即架着张经平缓缓朝着门外走去。
“大。。。。。。大哥。。。。。。”临近门口之际,张经平不知自何处得来的勇气,艰难地扭头看向许奕略带颤音道:“大。。。。。。大哥。。。。。。我。。。。。。我什么都说了,你。。。。。。您什么时候放了我啊。”
许奕恍若未闻般摆了摆手。
两名衙役见状,不再逗留,径直地架着张经平走出了刑具房。
“六爷。”赵守起身,将张经平签字画押后的供词送到许奕面前。
许奕伸手接过供词,缓缓查看起来。
事实上,张经平的供词并没有什么好看的。
供词如人一般,整张供词看似密密麻麻实则通篇只写着两个字。
那便是--吃人。
且吃人者尤不自知。
还以为自己只不过是做了所有纨绔子弟都会做的事情一般。
“呼~!”
许奕重重吐出一口浊气,随即缓缓将张经平的供词折叠后放入怀中。
这份供词固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