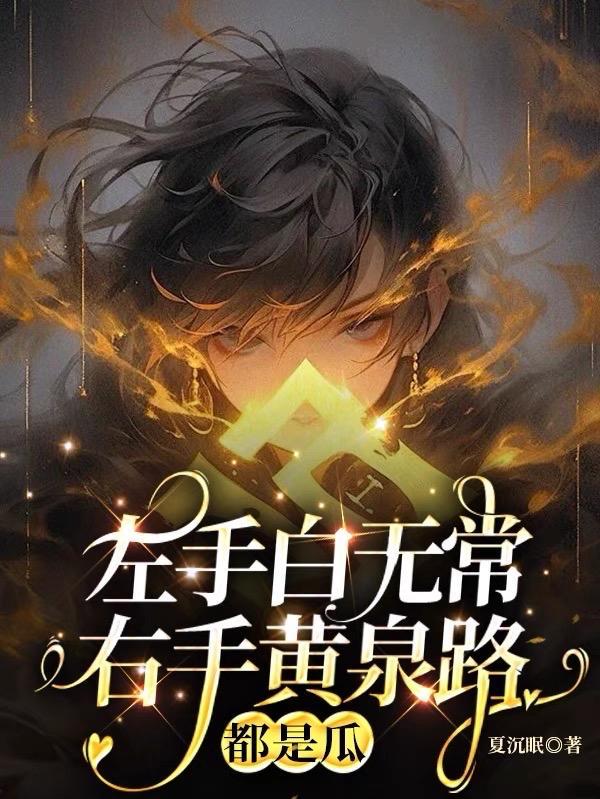笔趣小说>踹掉未婚夫的我改换甜文剧本笔趣阁 > 第4頁(第1页)
第4頁(第1页)
談畫的性格並不扭捏,這兩日的遭遇太過離奇,無怪乎她一時難以消化,再者她沒跟男人有過接觸,一上來就「深入」交流,難免吃不消。
她和賀為聿除了那層關係外不很熟悉,才會反應過度。
對上他莫名晦暗的眼神,談畫也發現了身上的痕跡,反正早就坦誠相待了,她不再遮遮掩掩,太做作不說,吃虧的人該是賀為聿,她總不能倒打一耙,乾巴巴地問:
「你有什麼事嗎?」
說完談畫就後悔了,這話像是她把人吃干抹淨了就要撇清關係,妥妥的渣女發言,可惜說出口的話不能撤回。
腦子太亂,為避免多說多錯,談畫沒解釋,而是靜待他的回答。
賀為聿杵在原地半天,終於有了點反應,他手裡拿著一管藥,抿了抿唇,溫聲道:
「你身上是不是不太舒服?我來給你上藥。」
相比於平時板著一張臉、表情不悲不喜、遇到任何事都從容冷靜的賀為聿,面前的人稱得上溫和,談畫不知道她被特殊對待,自然也發現不了差別。
以為冷淡是常態,對此接受度良好。
他方才出去接電話就是為了這個,特地諮詢院裡資歷老的醫生,對方以為他一早打電話過來有什麼要事,賀為聿默了幾秒才說明來意。
好在人家本來就是這方面的專家,什麼事沒遇見過,有些許的詫異,倒也沒過多地打,甚至和他交流幾句,仿佛面對的是尋常的病人。
反倒是賀為聿掛斷電話後紅了耳廓,從家裡常備的醫藥箱裡找出消炎軟膏。
談畫原先沒懂他的意思,眼睜睜看著他到床邊坐下,將被子掀開,雙腿察覺到涼意,她瑟縮了下,猛地反應過來,截住他伸過來的手,
「上什麼藥?」
甚至手腳並用,一隻腳抵在他腰際,阻止他靠近。
腳趾乾淨圓潤,透著淡粉色,羞得蜷了蜷,賀為聿沒生氣,想起她更為大膽的時刻,腿纏著他的腰,像彎曲而上的藤蔓。
談畫和他想到一塊去了,適逢下半身感覺涼颼颼的,看到他視線下移,猛地收了回去併攏雙腿,那雙冷凝的眼睛裡罕見地浮現出笑意,須臾之間便消失不見。
「我看了有些紅腫,塗藥會好得更快,免得等會難受。」
面對關心的話語,談畫蹬鼻子上臉,「那還不都是因為你……」
「抱歉,」他認錯的度讓她驚詫,「我不看,你忍一下,我很快就好。」
將藥膏的蓋子旋開,作勢要擠到手指上,這話怎麼聽怎麼不對勁,和在床上的聲音重合,談畫在心底感慨不愧是醫生,說起這些來臉不紅心不跳,她自愧不如。
情急之下她直接握住他的手,另一隻手奪過藥膏,「不用麻煩,我自己來。」
柔軟的觸感和傳來的溫度讓他怔了一瞬,按下心頭的躁動,面上沒有表現出半分,「你能看見嗎?」
表情和語氣都頗為正經,賀為聿似是不放心她,談畫不想談論這種話題,又躲不過,欲哭無淚道:「我不用看……我能找到的,你相信我。」
「那好,如果不行的話我再幫你。」
「嗯,」談畫想把人趕緊送走,等了半天沒見他有要挪動的跡象,急得開始趕人,也不顧這裡是賀為聿的地盤,「那什麼,你能不能先出去一下?」
饒是她臉皮再厚,也不能當著他的面做那麼羞恥的動作。
手一直緊緊捏著被子,賀為聿發現她指甲邊緣有乾涸的血跡,顧不得先回答她的問題,「疼不疼?」
流露出的關切和心疼讓談畫不明所以,順著他的視線看去,戰況激烈到她指甲都劈了,如果她沒猜錯的話,賀為聿的後背應該相當慘烈。
先前不覺得,被他這麼一說談畫還真的覺得有點刺痛,她本來就嬌氣,也不藏著掖著。
「疼。」
未嘗沒有撒嬌的嫌疑,賀為聿很快拿了醫藥箱過來,給她做簡要的處理,先用酒精消毒,原想塗完碘酒後纏上紗布,談畫覺得不方便,堅持貼了張創口貼。
「我去廚房做早餐。」
這回賀為聿有了自覺沒有多留,他起身,剛扶上把手便停下腳步,回過頭問她,「你知道我的名字嗎?」
帶著猶疑和不確定,他的眼睫微微垂下,加上有些距離,是以談畫揣測不到他內心的想法。
兩家是世交,原主和賀為謙是青梅竹馬,按道理和弟弟也會有交集,再怎樣不至於到連名字都不知道的地步,忽略那股怪異,談畫喚他,「賀為聿?」
尾音上揚,卻是肯定的語氣,猛地想起昨夜他問過類似的問題,那會她壓根沒心思理會,他的執著程度可見一斑。
賀為聿的手緊了緊,表情維持得很好,應了一聲將門帶上。
談畫手裡還拿著那管藥膏,冰涼的鋁箔包裝時刻彰顯著存在感,她彆扭地給自己上了藥,將目光移到床尾的紙袋上。
這是賀為聿拿過來的,說是給她買的衣服。
雖然方才和男主友好地會面,但談畫並不打算在這多待,她急需找個安靜的地方,好好捋清楚事情的來龍去脈,才好對接下來的事做進一步打算。
因此她飛快地穿好衣服,是一套粉白色的運動服,和她平時的穿衣風格很不相符,眼下沒條件挑剔,將拉鏈拉到最上方,適合用來遮掩身上的痕跡。
小貼士:如果覺得不錯,記得收藏網址或推薦給朋友哦~拜託啦(。&1t;)
&1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