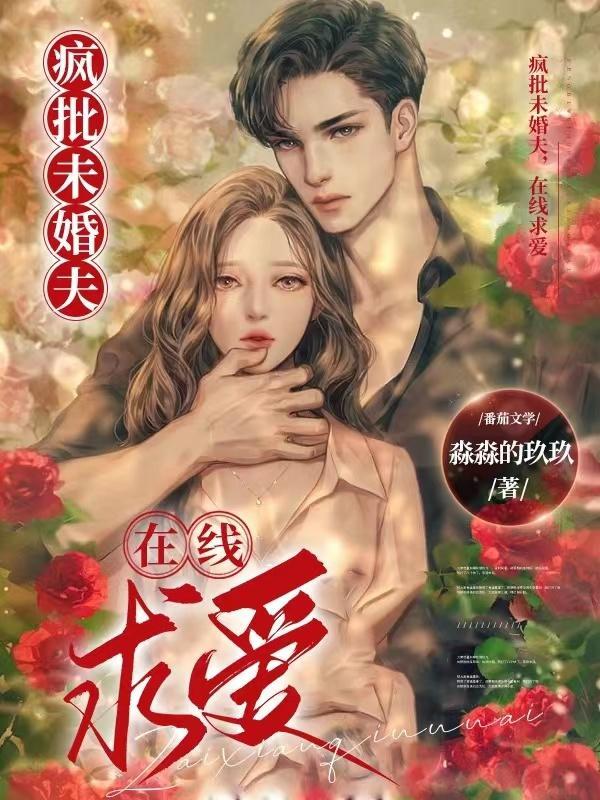笔趣小说>香凌 红楼梦 > 第6章(第1页)
第6章(第1页)
忽然,一个清亮的声音响起,“这位小兄弟,我见你面色发白,可是有晕船之症?”
甄栩勉强抬头看,一个面容清俊的少年正站在两步外。这少年约摸十岁多,想是刚开始抽条,身形有些瘦长,虽穿着身石青色衣袍,却已有几分风流品格。
那少年见甄栩不过七八岁大,生得明眸皓齿,比一般孩童沉静许多。看他半天不答话,便道“小兄弟莫怕,我叫冯渊,是金陵人,正要与父亲从姑苏回家去。你若是头晕,我让小厮去取些薄荷油来,涂在太阳穴上片刻便好。”
冯渊,这名字怎么有些耳熟?甄栩未及细想,娇杏在不远处唤他,“栩哥儿,太太叫你去吃饭呢!”
“多谢这位哥哥好意,母亲唤我,就不劳烦了。”甄栩对冯渊笑了笑。
随后的几日水路,甄栩头晕目眩,再没出房门,把那个冯渊冯小哥也给忘了个干净。
好不容易下了船,已是三日后。因着前主人急着上任,一应家具都折价变卖给了甄士隐,甄五和青竹早就把正房并东厢房收拾出来。
甄栩还不及看新宅子是何模样,便先昏睡过去。再醒来的时候,已是第二日晌午。甄栩见房中无人,叫良姜娇杏也无人应答,便走出门来。
这宅子比姑苏旧宅略小些,前主人想是无心布置,正院和花厅只有零星草木。甄栩走到抄手游廊上,见青竹正搬来他惯用的小书案,娇杏把英莲的东西都点出来。
搬家既已尘埃落定,他方觉得松了口气。接下来只要盯住金陵的府衙、人市和薛家即可。只是家中不过七八个仆从,还有两个留在姑苏看屋子,这人手着实有些不够。
甄栩正想找父母商量,忽听大门被拍得砰砰响。
案发
忽听大门被拍得砰砰响。
青竹把门打开,门口一人灰头土脸,形色凄惶,竟是留守姑苏的小厮谷芽。他衣角处有些焦黑,进门就摔了一跤趴在地上。
青竹把他扶起来“这是发生什么了,你怎么这么狼狈?如何不在姑苏守着院子,跑来金陵?”
谷芽大喊“不好了,不好了!老爷太太可在?”
封慧听到动静走出来,见他这般模样,吃了一惊“怎的如此吵闹,可是出什么事了?”
“太太,姑苏老宅被烧了!”谷芽哭道。
封慧愣了一下,颤声道“你说什么?”
“姑苏老宅被烧了!老爷太太走后第二日,那葫芦庙不知怎的着了,周围人家都竹子木头做的院墙,也接二连三烧了起来。官府老爷派了许多官兵救火,仍是烧了一夜。到了早上,整条街都成了瓦砾场,咱们家也没躲过!”说到此处,伤心地嚎啕大哭起来。
甄栩心中默叹,临走前嘱咐留守的小厮看好灯火,又让他们在院子里备足水,以免火灾。没想到这火并不是从自家宅子里烧起,而是场根本就躲不过去的灾祸。
“娘!”甄栩见封慧身子晃了一下,连忙和良姜把她扶住。“良姜,你快扶母亲进屋。青竹,你去请个大夫。”
听到幼子小大人似的安排,封慧稳住心神,拍了拍他的手,对青竹道:“我没事,不必去找大夫,你去把老爷请回来。”
原来士隐听栩哥儿说起,曾在梦中见英莲在应天府衙出现过,便与甄五去府衙打听。又因此认得了几个读书人,今日便是其中一位书生相邀。
甄栩陪着母亲回到正房,“娘亲,您别难过,姑苏旧宅虽然毁了,咱们好歹已经搬到了金陵,若是迟上两日,可就难说了。”
封慧此时也缓了过来,“我儿说得对,娘就是有些后怕,也不知道咱们那些旧邻都怎么样了。”
封慧虽心中还存着事,却不欲让儿子担忧“栩儿,姑苏旧宅之事你且放下,爹娘自会处理。倒是给你收拾的屋子,一应陈设可有什么短了的?”
“娘向来考虑的细致,哪里就缺了什么呢。”
“不缺便好,你这会子先去吃饭,再逛逛新宅子。往后,这儿就是咱们的家了。”
晚些时候,甄士隐得到消息赶回来,叫谷芽把事情详说一回。
又问他“官府可有说如何处置?”
谷芽道“县官老爷贴了告示,说咱们那条街没个几年清理不完,便让各家人登记了名册,自寻住处。申姜还守在那里,让我先回来报信了。”
封慧道:“孩子,你小小年纪便独自奔波,受苦了。你回来先去看看张妈,儿行千里母担忧,她这几日都念着你。”谷芽应是,便自去见张妈。
封慧和士隐私下叙话,“姑苏宅子一毁,咱们家一半的家资便没了,若不是因着要搬到金陵来,恐怕如今只能去住乡下的小庄子了。只是如今家中现银,买这宅子时便已用完,如今不过只够一个月开销。庄子也许久未送收成,恐怕得暂且变卖书画度日。”
甄士隐道“也只好如此罢了,明日便先去当几样东西,晚些再派人去查看庄子的情况。”
次日,着人打听过裱画廊、书铺、当铺的聚集之处,甄士隐与甄五带着几册古画便往三山街去。
将要出门,听得一声“父亲!”
原来是甄栩已经穿戴齐整,磨着士隐要一同前去。老来得子,士隐原就视若珠宝,如今更是有些溺爱了。见儿子非要出门,只好答应“如此,爹抱着你。”
“儿子自己能走。爹爹放心,我跟紧您。”甄栩有些哭笑不得,但也晓得父亲是怕自个儿也走丢了,只得抓住士隐的袖子。
因甄士隐不忍卖掉旧物,两幅古画只是活当,换了五十多两银子。家中用度暂且有了着落,士隐便带着儿子逛起金陵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