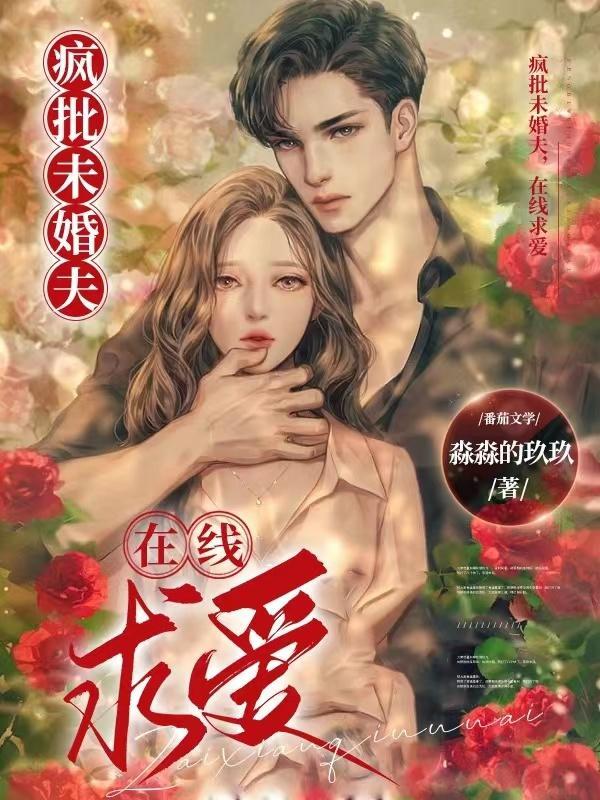笔趣小说>红楼香菱百度百科 > 第90章(第1页)
第90章(第1页)
次日一早,甄栩照常去兵部衙门上值。才进了院子,就听有几个小吏在私下八卦:“昨日便听说贵妃娘娘临盆,怎么到了今早了,还没有龙子的消息呢?”
一个小吏悄声道:“我有个亲戚是太医院的,今早我才碰到他,他说娘娘折腾了一夜,龙子还未降生呢。”
另一个小吏恍然大悟:”都传说贵妃娘娘这胎是双生子,我还道双生子不详,莫不是后宫争宠传出来的闲话。如今听你这么一说,倒觉得这传言像是真的。”
前面那人又压低了声音:“这话可不兴说,就算是双生子,咱们也得当成是一胎一个的。”
甄栩听到这里,走过去道:“你们一大早不做事,在这里传皇家私事,也不怕被人抓住要挨板子?”
那几个小吏吓了一跳,待看到是甄栩又松了口气。小甄大人向来和气,若是其他老大人,他们可能就得吃不了兜着走了。
几个小吏异口同声:”甄侍郎早!我们这就去干活,再不敢闲话了,还望甄侍郎不要怪罪。”就听甄栩道:“下不为例。”
小吏们忙点头答应,见甄栩走了,才又小声道:“还好是小甄大人。”
另一人想起什么,拍了下头:“可是小甄大人的太太好像是贵妃娘娘的表妹——”
一个灰衣裳的小吏连忙打断:“好了好了,别说了,甄大人看起来再年轻好说话,也是在战场拼杀过的,你们当他真是个好拿捏的,还敢扯到他夫人!”
几个小吏听了这才住了嘴一哄而散。
文渊殿
几位阁臣已经在殿中已经等了半个时辰,仍未见皇帝的影子。次辅申春林是个急性子,把站在殿外的内侍问了四五回。
首辅赵泽之看着他转来转去,安抚道:“申阁老,你就坐下等等吧,你这转的我头都要晕了。”
申春林有些暴躁:“部里还有一大堆事情,且还都是急事,我能不着急吗!”
忽听有人道:“申爱卿,是什么事这么急,说与朕听听?”
几位阁老听见这声音,都立刻站起来:“见过皇上。”
皇帝挥手让他们坐下:“今日是朕之不是,虽然朕不是第一次要做父亲,可毕竟是皇家子嗣,朕便多守了一会儿。”
赵泽之立即道:“皇上牵挂娘娘和皇子,本是人之常情。如今为了百姓和国事,又不得陪在贵妃娘娘身边。申大人平日就是个炮仗,为了公事没少着急上头。可见皇上与申大人都是出于公心,千百年后定然又是一桩君臣美谈呐”
皇帝本来因为贵妃生产不顺,心中不快,听了这番话,哈哈大笑:“好个君臣美谈!申爱卿且把事情细细说来吧。”
申春林向赵泽之微微点头,对皇帝道:“陛下,自先皇在位时,户部便银钱紧张,一直勉强维持收支平衡。西海沿子几场大战下来,更是快把国库存银都耗光了。这几年水患频发,水利重新兴修迫在眉睫,户部却几乎支不出银子。再有眼下盐政的情况,竟是个收的愈发少,支出愈发多的局面。”
他犹豫了一下,还是说道:“依臣之见,近年来两广的商船众多。咱们如今只准丝绸、茶叶、陶瓷、药材四类外销,可依臣看,那些往来船只必有夹带。不若再多放开外贸的种类,增加朝廷税收。”
皇帝的手指敲了敲桌子,没有表态。
赵泽之道:“臣却有不同的意见。”
皇帝有些惊讶:“哦,爱卿可是不赞同申爱卿所言。”
赵泽之拱手道:“岭南盐业繁荣,可朝廷却几乎对岭南盐场没有控制力,若是能把岭南盐场的税都收上来——依臣看,盐政改革除了要从西海卫所动刀子,也该从两广入手。”
皇帝颔首:“既然两位爱卿都视岭南为财政之要害,那派谁去岭南处理此事为佳?”
这可让几人一时犯了难。赵泽之道:“这趟差事,既有户部所涉之外贸事宜,又牵涉与兵部挂钩的盐政改革,且又路途遥远,必得寻个年富力强、又在户部和兵部任过职的人方可。”
几人听了,脑海里都立刻浮现出一张令人如沐春风的年轻人面孔。
甄栩下了值又去了趟路府,仍是不见路煜回来。他心中虽然有些着急,不过皇帝赐婚必然是挑路煜在京的日子,倒不必担心路煜回来前婚事就被定下。
回到家中,晚饭时看到浅笑的英莲,甄栩心上一阵愧疚。感觉到黛玉悄悄捏了捏他的手,甄栩向她笑了笑。
封慧见他们吃饭时仍旧眉目含情,知道小两口感情极好,心中宽慰。
这时,却有门上的人前来通报:“老爷太太,门口来了位抱着孩子的年轻姑娘,说是要见少爷!”
封慧才刚觉着儿子儿媳感情好,这下听到有个带着孩子的姑娘来找儿子,一瞬间慌了神。
好半晌,她才回过神来责备地瞪了眼甄栩,又安抚黛玉道:“媳妇放心,栩儿应当不是那种拈花惹草的人。若真是他被外室找上门来,我先替你收拾他!”
甄栩也是摸不着头脑,他连忙道:“母亲你胡说什么呢,人家又没说那孩子是我的,怎的您先往我头上泼脏水。”
说罢他又向黛玉摊了摊手,语气十分无辜:“我一向公务繁忙,哪有空养外室?黛玉,你是知道我的。”
访客
京城今日消息灵通的人都晓得,皇家有喜事发生,贵妃娘娘膝下添了个皇子。
当今圣上之前就一个病恹恹的太子,众臣只怕太子立不住,以后又要在宗嗣里选人。可嫡系一脉人丁单薄,宗嗣都出了五服,若要选人,恐怕又是一场大乱。如今贵妃娘娘生了个健康的儿子,臣僚们都松了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