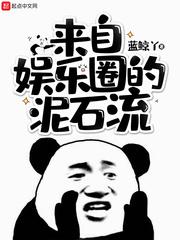笔趣小说>逍遥第一本秘籍学什么 > 第12章 举动(第1页)
第12章 举动(第1页)
李府一家人坐在中院的正厅,没有一个人说话,李平风坐在主位默默的抽着烟。李长空换了身衣服坐在下,对面是李瀚雄夫妇。
这时候战疯手里拿着一张大到夸张的弓从外院跑进来,看见这种情况,挠头说:“是不是来晚了。。。。。。这张弓藏的太深了,找了好久。。。。。。”李平风放下了烟袋,手里重新装着烟丝:“没事了,老林和赵麻子你都安排人掩埋了吧。。。入土为安,让弟兄们今夜打起精神别再出事了”
战疯手拿着弓一抱拳:“是!义父!抓起来的人怎么办?就这样关着?”李平风眼里罕见的露出了凶狠的神色:“这么多年忍气吞声,反而搞得我家乌烟瘴气,明天在大门口全砍了!另外命令城外的护卫队,明日进城,把刀子给我磨好!”
“爹!”李翰雄有些疑惑不定:“这样是不是不太稳妥,是不是先和宫里那位通通气!”“又不是打仗,请教什么!除了马的重甲和长兵器不带,去对面西市租一间客栈给他们!这件事就这么定了!”李平风将烟袋用力的拍在桌子上!
“是!”战疯一拳擂在胸口转身离去,竟然行的是军礼!
等战疯下去,房间又恢复了安静,最先开口的是李长空,担忧的说:“爷爷,你还好吗?”李长空摆了摆手:“没事,旧伤,今日一急反倒是这口浊气吐了出来。还让我有所精进!好事来的!”李长空点点头继续说:“那就好!今日之事,处处透着诡异,本来想抓几个暗子,结果跑出来犬戎的密谍,还有老林头临死前说的那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似乎和我爹有关?”
五年前,李翰英出事之后,李平风带着军队在犬戎像犁地一样的翻了几千里,也是直接打痛了犬戎,这几年消停了许多。但是今日才现,身边竟然隐藏了犬戎的密探,还是两个!他们潜伏了多久?做了什么?今日为什么会暴露自己?一大堆疑问充斥在众人的心中。
李翰雄也是点头:“黑阁的人不会莫名的出现,今天之事多半是意外撞在一起了。若不是那个家丁机敏,这两人还不知道要潜藏多久呢!”李平风整个人靠在太师椅上如同睡着一般,眼睛里却是精光闪烁:“据战疯说,赵麻子怀里当时有不少银钱,一个密探,身上带着这么多钱,只有一个原因:要离开这里!当时又为什么要暴露自己?老林不惜暴露自己也要杀了赵麻子,这赵麻子身上肯定有什么秘密。。。。。。”
这件事就像一团乱麻,没有任何的头绪,这时候李长空蓦得打断了李长空的话:“爷爷,赵麻子和老林的事可以容后再说,此时还有几个事要做!”作为前世科技达各种情报战中,李长空都是其中的佼佼者,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掩盖这两个人已经暴露的事实,让他们合理的死亡,不要惊动剩下的人。突然暴露,他们的东西肯定来不及这转移,肯定是能留下一些线索的。
李平风没有怪自己的孙子打断他,反而很赞赏自己的孙子,李家的子孙就没有废物!几个人就这件事又商量了很久,才散去,
今夜的李府大多数人都无法入睡,当然有个人除外,那就是被踢晕过去的胡八斤。。。。。。
。。。。。。
第二日,整个京城生了一件爆炸性的新闻,镇北王府门口,五花大绑了六个人,跪在门口。背后站着一排凶神恶煞的家丁,身着黑色皮甲,头戴圆盔,黑色武士裤,脚蹬战靴,俨然一副轻装步兵的打扮。
京城的官邸基本都在万年县通义坊这边,一来是安静,环境好,二来是与皇宫离得近,还有就是风水之说。还有就是皇帝宣见、上朝都方便。
李府位于通义坊和西市的交接处,也是当初被人穿小鞋才把李府建在这里。李府的右手边就是通义坊众多的官邸,左手边就是西市的酒楼和市场,十分热闹。所以一大早李府门口就被围得水泄不通。
别人的府邸普通民众都是敬而远之,李府不一样,李府在这附近秋毫无犯不说,冬季还有施粥给那些无家可归的人。老夫人徐珏心慈,偶尔还会收留一些人。
今天看到李府门口跪了这么多人的时候,就都围了过来。看热闹是人的天性,只有少数人现了,李家的护卫,今天穿的很不一样。更重要的是手里拿的不是哨棒,是镇北军标志性的长刀,镇北军的刀是无鞘的,平时背负在身后,与盔甲的机括相连,便于空出双手使用长枪。用了特殊处理,呈暗黑色,形状像放大的雁翎刀,刀柄可双手握持,这是为了对付骑兵衍生的武器,只有镇北军中才有,没有正式名称,对军人来说,能砍死人让自己能活命就比什么都强,有好事者起名为镇北刀,渐渐的就叫镇北刀。
66续续人越来越多,战疯扛着刀站在门口,一只独眼锐利的扫着四周。今日之事,义父已经交代了,天王老子来了也不行,对于义父的命令,战疯向来是不打折扣的。独眼扫过,现人群后面已经来了三辆黑色的马车,停在街对面,以战疯的目力自然能看清马车左上角的标志。一只雨燕那是域查司的标志,一个是一个圈里面画了一个长柄斧,哼,护龙卫,手还真是伸的够长,还有一辆马车通体黑色,车窗也是黑布遮盖,不知是哪家的。斜对面的四层酒楼,二三四层楼都有人往这边探望。看来是不方便露面或者想暗中观察的势力。
战疯用力的吸了口气,只有拿着威刀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活着,平日拿着哨棒被人瞧不起。战疯不是不知道义父一直在避嫌想要低调,昨晚上却让城外的护卫全副武装进城,不知道这么高调是为什么。不过想不通的事情就不想,有人为难义父,一刀砍了便是。战疯恶狠狠的想到。
李府一家人坐在中院的正厅,没有一个人说话,李平风坐在主位默默的抽着烟。李长空换了身衣服坐在下,对面是李瀚雄夫妇。
这时候战疯手里拿着一张大到夸张的弓从外院跑进来,看见这种情况,挠头说:“是不是来晚了。。。。。。这张弓藏的太深了,找了好久。。。。。。”李平风放下了烟袋,手里重新装着烟丝:“没事了,老林和赵麻子你都安排人掩埋了吧。。。入土为安,让弟兄们今夜打起精神别再出事了”
战疯手拿着弓一抱拳:“是!义父!抓起来的人怎么办?就这样关着?”李平风眼里罕见的露出了凶狠的神色:“这么多年忍气吞声,反而搞得我家乌烟瘴气,明天在大门口全砍了!另外命令城外的护卫队,明日进城,把刀子给我磨好!”
“爹!”李翰雄有些疑惑不定:“这样是不是不太稳妥,是不是先和宫里那位通通气!”“又不是打仗,请教什么!除了马的重甲和长兵器不带,去对面西市租一间客栈给他们!这件事就这么定了!”李平风将烟袋用力的拍在桌子上!
“是!”战疯一拳擂在胸口转身离去,竟然行的是军礼!
等战疯下去,房间又恢复了安静,最先开口的是李长空,担忧的说:“爷爷,你还好吗?”李长空摆了摆手:“没事,旧伤,今日一急反倒是这口浊气吐了出来。还让我有所精进!好事来的!”李长空点点头继续说:“那就好!今日之事,处处透着诡异,本来想抓几个暗子,结果跑出来犬戎的密谍,还有老林头临死前说的那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似乎和我爹有关?”
五年前,李翰英出事之后,李平风带着军队在犬戎像犁地一样的翻了几千里,也是直接打痛了犬戎,这几年消停了许多。但是今日才现,身边竟然隐藏了犬戎的密探,还是两个!他们潜伏了多久?做了什么?今日为什么会暴露自己?一大堆疑问充斥在众人的心中。
李翰雄也是点头:“黑阁的人不会莫名的出现,今天之事多半是意外撞在一起了。若不是那个家丁机敏,这两人还不知道要潜藏多久呢!”李平风整个人靠在太师椅上如同睡着一般,眼睛里却是精光闪烁:“据战疯说,赵麻子怀里当时有不少银钱,一个密探,身上带着这么多钱,只有一个原因:要离开这里!当时又为什么要暴露自己?老林不惜暴露自己也要杀了赵麻子,这赵麻子身上肯定有什么秘密。。。。。。”
这件事就像一团乱麻,没有任何的头绪,这时候李长空蓦得打断了李长空的话:“爷爷,赵麻子和老林的事可以容后再说,此时还有几个事要做!”作为前世科技达各种情报战中,李长空都是其中的佼佼者,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掩盖这两个人已经暴露的事实,让他们合理的死亡,不要惊动剩下的人。突然暴露,他们的东西肯定来不及这转移,肯定是能留下一些线索的。
李平风没有怪自己的孙子打断他,反而很赞赏自己的孙子,李家的子孙就没有废物!几个人就这件事又商量了很久,才散去,
今夜的李府大多数人都无法入睡,当然有个人除外,那就是被踢晕过去的胡八斤。。。。。。
。。。。。。
第二日,整个京城生了一件爆炸性的新闻,镇北王府门口,五花大绑了六个人,跪在门口。背后站着一排凶神恶煞的家丁,身着黑色皮甲,头戴圆盔,黑色武士裤,脚蹬战靴,俨然一副轻装步兵的打扮。
京城的官邸基本都在万年县通义坊这边,一来是安静,环境好,二来是与皇宫离得近,还有就是风水之说。还有就是皇帝宣见、上朝都方便。
李府位于通义坊和西市的交接处,也是当初被人穿小鞋才把李府建在这里。李府的右手边就是通义坊众多的官邸,左手边就是西市的酒楼和市场,十分热闹。所以一大早李府门口就被围得水泄不通。
别人的府邸普通民众都是敬而远之,李府不一样,李府在这附近秋毫无犯不说,冬季还有施粥给那些无家可归的人。老夫人徐珏心慈,偶尔还会收留一些人。
今天看到李府门口跪了这么多人的时候,就都围了过来。看热闹是人的天性,只有少数人现了,李家的护卫,今天穿的很不一样。更重要的是手里拿的不是哨棒,是镇北军标志性的长刀,镇北军的刀是无鞘的,平时背负在身后,与盔甲的机括相连,便于空出双手使用长枪。用了特殊处理,呈暗黑色,形状像放大的雁翎刀,刀柄可双手握持,这是为了对付骑兵衍生的武器,只有镇北军中才有,没有正式名称,对军人来说,能砍死人让自己能活命就比什么都强,有好事者起名为镇北刀,渐渐的就叫镇北刀。
66续续人越来越多,战疯扛着刀站在门口,一只独眼锐利的扫着四周。今日之事,义父已经交代了,天王老子来了也不行,对于义父的命令,战疯向来是不打折扣的。独眼扫过,现人群后面已经来了三辆黑色的马车,停在街对面,以战疯的目力自然能看清马车左上角的标志。一只雨燕那是域查司的标志,一个是一个圈里面画了一个长柄斧,哼,护龙卫,手还真是伸的够长,还有一辆马车通体黑色,车窗也是黑布遮盖,不知是哪家的。斜对面的四层酒楼,二三四层楼都有人往这边探望。看来是不方便露面或者想暗中观察的势力。
战疯用力的吸了口气,只有拿着威刀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活着,平日拿着哨棒被人瞧不起。战疯不是不知道义父一直在避嫌想要低调,昨晚上却让城外的护卫全副武装进城,不知道这么高调是为什么。不过想不通的事情就不想,有人为难义父,一刀砍了便是。战疯恶狠狠的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