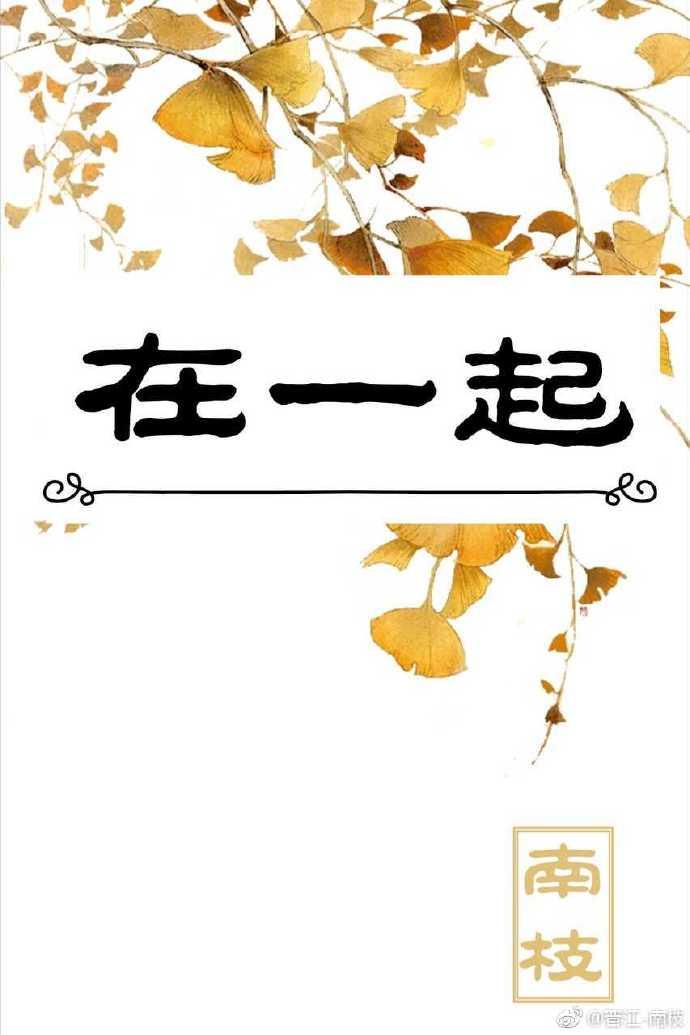笔趣小说>450. 第450章 身不由己[娱乐圈 > 第4章(第1页)
第4章(第1页)
门外守着的两人为宣王府的特殊侍卫,林琅派他们守着君钰,一是因为这两人有着死士的忠诚,二是因这两人曾蒙君钰的恩情,对于君钰自会照顾得当。
君钰抓着床帐子,汗水再一次模糊了他的视线,忍着痛楚尽量使自己的声音平静,道:“无事……”
跌跌撞撞地坐回床沿,君钰一手抓着床帐子,一手抚着腹部。似乎有些呼吸困难,君钰挺了挺腰,揉抚着肚子闭着眼睛喘了一阵。
褪去层层衣衫的腰腹间十分显眼地拱起了一个半大的圆弧,随着君钰的一呼一吸间起伏不停,那指如葱根的手掌在上面打着圈来回安抚着。
这种扶腰抚腹的脆弱姿势,若是在人前,他自是宁死也不会做出来。
许久,感觉腹中不再那麽闹腾,视线也清楚了许多,君钰才小心地扶着腰站起来,慢慢踱步向外堂过去。
行走间,君钰的步履略微蹒跚,腹中的活物月份已大,便撑得腿脚不自觉地向外迈开,不过君钰总爱穿广袖宽袍,长及脚踝的衣摆下,他不自然的步子,若不是极亲近的人细看,也瞧不出什麽来。
扶着桌案,君钰慢慢坐下,桌上整整齐齐地摆了四碟精致的小菜、两盘糕点、一碗米饭,以及一玉壶酒。
闻得那浓郁的酒香,君钰便给自己倒了一杯,酒水流过口腔中的每一处角落,清冽醇香,幽幽透着几缕梅花香的辣味,熟悉的味道叫君钰倏忽眼睫一湿,但终究他是没有落下泪来。
桌上皆是自己平日爱吃的菜品,君钰不自觉便多倒了几杯,碍于自己现下的身体不宜多饮,君钰饮了几杯,便适可而止地放下酒盅。
一日未进食,加上之前的呕吐,君钰早已饿得不行,只是,望着桌上精致的菜点,他却又实在无甚胃口,草草吃了几口,便放下了筷子。
却是此时,一把冷如寒铁般的声音幽幽响起:“外头为宣王大婚大肆庆祝、热闹非凡,君大人为太尉大人的亲弟、大秦的右将军,更为宣王的恩师,大人现下在此偏僻小院内独自斟饮,是否不合时宜?”
在清净到空旷的房间里,这声音的寒凉和突然,让人生生打了个寒颤。
君钰侧首,便见一华服玉带之人立于门旁。那人身形高大,相貌堂堂,宽大的礼服下仍然保持着军人如松般的站姿,刀削般的眉宇间自有一股不怒自威的威慑力。
屋子的大门紧紧关闭着,显然并非是刚刚重新开啓过——想来那人站在那处已是有一段时间了。
“君大人用不着向门外瞧,我既然能站在这里,自然有办法让外面的两个废物闭嘴的。”那人说着便大步走到桌前,掀起衣袍坐下,毫不客气地为自己斟酒一杯,一口饮下,那人赞道:“好酒!醇香清冽,饮如小火蕴烧,又多一缕梅香寒幽,没想到宣王竟藏了此等佳酿!”
“蔡大人来此,有何贵干?”君钰漂亮的眉目未动一分,好似波澜不惊问道。
眼前这人名为蔡介,字子明,是颍州镇远侯之子,当朝的左将军,亦是今日的宣王妃一母同胞的兄长。
“听闻故人归来,我自然是前来叙旧的。君大人并未就义于断崖,蔡子明心中甚是欣喜。”蔡介目光一转,落在君钰桌案下的肚腹上,“只是数月不见,君大人似乎变化颇多。”
君钰未曾想到蔡介会来,因着屋子里着了暖具,现下君钰便未穿外衫,内里只着了两件薄衫,他人一眼望去,君钰坐姿下隆起的肚腹身形明显,一览无余。
君钰顺着蔡介犀利的目光微不可见地颤了颤,但很快恢複,君钰一语不发,装作无事发生,只冷眼瞧着蔡介拿了自己的酒杯,斟了一杯又一杯。待他喝够,君钰才缓缓道:“叙旧叙完了。今日宣王大婚,蔡大人为王妃兄长,想来也不能缺席太久。”
“君大人,你还没喝酒,怎麽能说叙完旧了呢?”蔡介又将他喝过的酒杯斟满,举到君钰的面前,“君大人,请。”
君钰冷眼看他,纹丝不动,道:“如此时候蔡大人不去招呼衆宾客,却来这处偏僻之地,我想不会只是为了叙旧那麽简单吧。”
蔡介举着杯子干笑:“君大人认为我能有何目的?”
君钰道:“在下不知。”
“若我说,我确实是来与君大人叙旧的呢?”
君钰反问道:“蔡将军当我三岁孩子吗?”
蔡介似笑非笑地哼笑了一声,一口饮尽手中举了半天的酒,将杯子倒举了在君钰面前,道:“岂敢。君大人怎的如此紧张?为何今日君大人如此沉不住气,竟与本将军聊几句都不可了?昔日你与本将军在长离亭痛饮三天,舍命陪君子的豪情去了哪里?”
君钰不语。
“君大人在害怕什麽?”烛光映衬下,蔡介目光瞥来,君钰那微微敞开的领口,清晰可见皓白肌肤包裹着的精致锁骨,深衣下的身子在腰腹处鼓起一个臃肿的弧度,却越发显得他整个身体不同往日的单薄,“君大人既敢诈死,想来也思虑过后果,现在又有什麽好怕?”
顿了顿,蔡介继续道:“我颍川蔡氏与君氏昔日交好的情谊还在,现下又同宣王联姻,君大人该无须顾虑蔡某会从君大人此处得到君氏的什麽好处。”
君钰冷笑道:“你迫使我杀王谢之之前与我酒饮,也曾道你对我绝对不会有欺瞒。结果呢?”
“王谢之对你有浅薄的提携之情,我知晓你不忍心,那战你不杀他,他也会杀了你我,我骗你,也是无奈之举。”
“若非你想替代王谢之,便不会有那场屠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