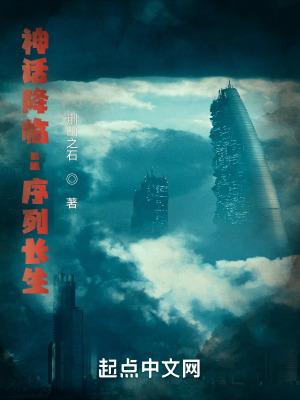笔趣小说>夫君他口是心非千山绿雪 > 第51章(第1页)
第51章(第1页)
好熟悉的名字。
裴朗宜想了想,听晋明琢提醒:“是那个岑伯父死后,没两年反倒高升都察院的下属。”
“是他?”裴朗宜恍然,想起他手底下的人还赞叹过齐东来为官十分了得,从获罪被贬职,到任职京中,只用了短短两年时间。
“我这次换回来的时机真差,正要跟那头的你说这事。”
晋明琢终究还是忍不了身上这惨不忍睹的衣服,站起来往里屋走去。
“就只有这点?”
见她挑起帘子,裴朗宜疑惑地问。
“还有净云的父亲,以及京郊的黄庄。”
晋明琢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裴朗宜跟着走到里屋去。
见她脱掉了身上那件外衣,打开衣橱,挑起了衣裳。
裴朗宜见状愣了愣,嘲笑她:“娇气鬼。”
晋明琢不甘示弱地回头瞪他,换了一件水蓝的,还到铜镜前照了照。
“行了别照了,洛神下凡。”
裴朗宜弯起嘴角说着不耐烦的话,“我也有话没来得及说,不过说给如今的你也一样。”
“什么事?”
晋明琢抚住他的臂,同他一起走到外间。
裴朗宜垂眸,带着一丝痛苦沉声开口:“小心我如今的上司。”
“冯大人?”
晋明琢吃了一惊,见裴朗宜沉默在那里,也没有说话。
桌上这把茶壶都是冯大人送给他的。
晋明琢端起来,疾步放到了外头,回来时嘴角弯弯:“当年被单夫子打手板时,那去肿的药膏是你送的?”
“你以为呢?”
裴朗宜抬头看她,语气理所当然。
见她拿来了一把新茶壶,那茶壶碧地像玉,雕饰又像一朵荷花,仿佛一朵绿莲,捧在晋明琢的手心。
“我以为都是慎玉送的。”晋明琢声音低低的。
裴朗宜嗤笑一声,也不计较。
也没什么可以计较的,人不能跟死者计较,裴朗宜明白,晋明琢也知道。
“膏药再好有什么用?都治不好你这条腿。”
裴朗宜疼惜地隔着衣裙,攥住了她的膝盖骨“我倒希望你日后还能爬树。”
晋明琢噗嗤笑出来,“哪有你这么当王爷的,撺掇王妃爬树翻墙的。”
深情没两分钟,又变成了抬杠。
他们夫妇二人,似乎特别擅长把一切的情深藏在针锋相对里。
便听裴朗宜摇摇头,一本正经地阴阳怪气:“我只不过说了句爬树,你倒是连翻墙都想着了。”
这是什么锱铢必较的回嘴方法,晋明琢哑口无言。
沉默片刻,听他正经地说:“我最近又寻觅着一位神医的踪迹了,等找到了请来给你治腿。”
哪里有那么多神医,晋明琢苦笑。
见她没有第一时间应声,裴朗宜不高兴地“啧”了一声,语气加重了又问一遍:“听到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