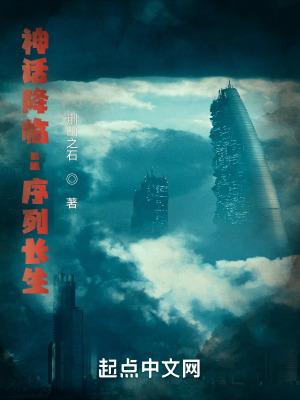笔趣小说>夫君他口是心非千山绿雪 > 第35章(第1页)
第35章(第1页)
“等会儿他们砍够了,歇一歇脚,我们便到山坡上去折松枝。”夏净云将水囊递给晋明琢,“这山上好像还有个小庙来着。”
晋明琢正拔出水囊的塞子,不想这么轻易地就有了话头,她捏了捏那木塞,不经意地问:“说起来,净云,你知道禅房吗?”
“禅房?花柳巷那个?”夏净云问。
“嗯。”晋明琢点点头,觉得有些口干舌燥,她喝了一口水,说道:“听说从前红极一时来着,我八九岁上才来的咱们这,所以知道的不多。”
夏净云不疑有他,点头道:“我小时候还真去过。”
见晋明琢来了精神,只当她一向好奇,也乐得继续说下去。
她回忆了一下,道:“我小时候身体不好,叫那和尚开了方子,往后吃着,到现在身子好多了。”
“是真的大有效果。”
她不由得替那禅房里臭名昭着的和尚说两句好话,又颇有些惋惜地说:“后来那些事我也听说了,我倒是觉得前后差别之大,倒像是换了一个人。”
晋明琢默默地记在心里,不是从出生一起长大的,倒真不知道夏净云身上还有这些事,她感叹了一句:“完全看不出来。”
又敏锐地抓住了重点,问道:“往后你现在还在用那个方子?”
“是啊。”夏净云点头,不疑有它。
晋明琢看向夏净云的眼睛,那是信她帮她,与她一起长了许多年的朋友,可她却在试探她,借着她调查她的父亲。
万一夏伯伯真与人勾结晋明琢攥紧了手心,不敢去想。
她补救般地,接了一句:“那真的用了好多年。”
-
那头,裴朗宜人到了藩司衙门。
时间不等人,老天爷下雨也是说下就下。
岑父着手开始着手修缮堤坝的事宜,征召民工,叫人贴了告示在城中,写明了待遇工酬。
见堂中人来人往,裴朗宜拉住岑父,“岑大人,我们借一步说话。”
叫的是官称而非亲称,自然是朝中的事。
岑父不敢大意,带着裴朗宜到了书房,禀退了左右。
“我今早收到了加急的旨意。”
裴朗宜从袖中拿出了那道圣旨,岑父朝东边礼了礼,这才接过。
“皇上的态度是此事得暗中察,银两的缺口先用省内的税收,待找到那不翼而飞的银子再补上。”
岑父边看,裴朗宜边说,待他看完了,定论:“这道旨意没什么助力,只是护身符罢了。”
“如此,还要岑大人多担待。”裴朗宜道。
“不敢,替圣上分忧,是臣等该做的。”
岑父抱了抱拳,又道:“晋大人在前头盯着招工,夏大人那头那没什么消息,不知小王爷的人可有什么进展?”
裴朗宜一点头,“长乔来报说,户部上头似是并不知此事,负责同柳贺良对接的人从始至终,都是同一个人。”
“何人?”
“这人倒真的大胆,也跟着押送队伍来了。”
裴朗宜嘲讽地笑了笑,“正是那车队里,负责队尾的小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