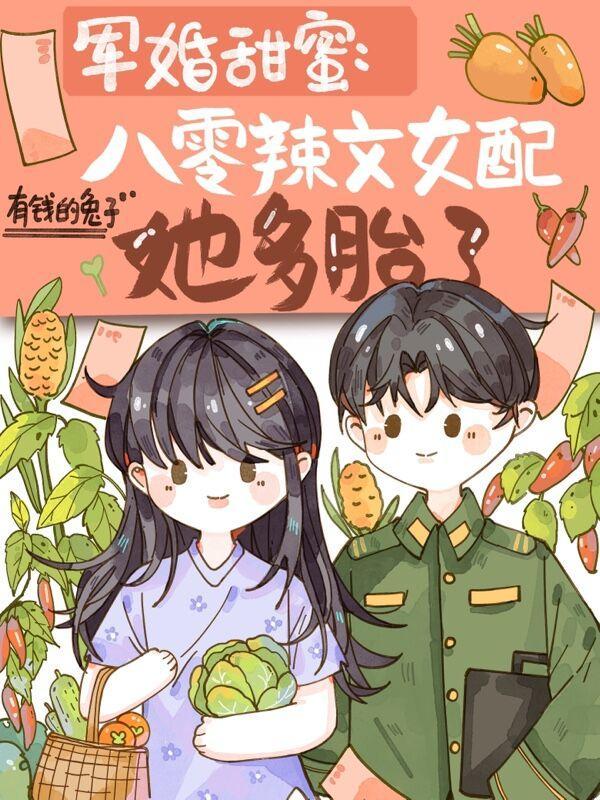笔趣小说>地乌金的功效与作用 > 第66章(第2页)
第66章(第2页)
她像是完全不为工作忙碌,也不怕丢了饭碗。
甚至于,在自己和罗敷朝夕相处的那段时间里。季庭柯从未看到对方联系过任何有关、“地方台工作”的电话。
休假也好、带薪调查也好。
一次也没有。
过于反常、过于蹊跷。
季庭柯心中,萌生了一个极其大胆、荒谬的猜测。
他原先都快略过了。但罗敷探究、追问的目光就堵在眼前。
她像是在鼓励他问——
于是,那寡言的男人艰涩、无据地:
“什么时候的事?”
罗敷装听不懂。
她装傻、直愣愣地问:“什么——什么时候的事?”
季庭柯看着她,不躲闪、不逃避。
“我是说。你是什么时候,脱掉了那层身份?”
“罗记者,那一层身份。”
话一问出口,罗敷身上就像是过了层电流。
她轻轻抖着,分不清究竟是紧张、还是兴奋。
她起初还不肯认。
但在季庭柯有些阴的目光下,她的眉头轻轻皱着、只扛了不到十分钟。
十分钟后,罗敷抬头看他:
“你瞒我瞒。我揭穿你,你也揭穿我。”
她说:“有意思么,仲庭柯?”
她对他的称呼发生了变化。
季庭柯慢慢地眯起眼睛,尽量逼自己去忽视那个突变的姓氏。
他继而重复,语气更加严厉:
“什么时候?”
罗敷不怵他发火。
她点了根烟,看着烟雾盘旋而上。
良久,她才找回了自己的声音:
“在来这里、来西山之前。”
季庭柯松泄了绷紧的肩线,他的喉咙像被什么堵着、只能听到罗敷自说自话的声音。
她说:党媒工作,唯领导是论。
“领导说有新闻价值,我就得外采写稿。他说不在职责内,我就必须放弃&039;郝国平&039;的爆炸案相关。”
“我这样的人,永远无法都通过职场服从性测试。就像你、永远都学不会服软一样。”
“我们俩,都是硬骨头。”
过去身在其位的罗敷,需要遵守狗屁规章、需要听从上级教诲。
她不能为郝国平申冤,不能跃进火海、探寻真相。
但眼前、当下的罗敷,是恢复自由身的罗敷。
她可以擅自来往西山,可以光明正大地,为自己、为更多人,解开这宗谜团。
罗敷忍着笑,她瞄了一眼季庭柯:
“不好笑吗?”
“我早就不是罗记者了。而你,从来也不是季庭柯。”
她满嘴的谎言,他一身的秘密。
两个自以为是的骗子。
罗敷抬手,轻轻碰了碰季庭柯的鼻尖。
她说:说谎的人,鼻子是会变长的
季庭柯沉默了两秒。他放空目光,低声说了一句:
“你有没有听说过,有一种硫化物矿物、叫——愚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