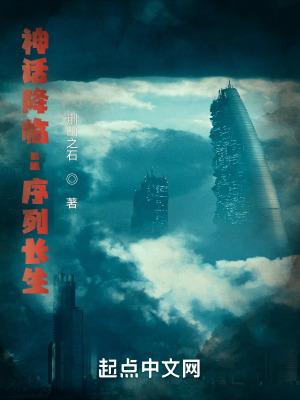笔趣小说>一如既往的冷漠是什么歌 > 第71章(第1页)
第71章(第1页)
“汤米?”电话里的男声是那样遥远。
“大事不妙!塞尔吉奥没在圣心圣心花园街……出来的是个女人,妈的她被炸死了!”汤米一拳捶裂电话亭的玻璃,裂痕从被攻击处裂到另一个格子。
文森佐第一次听到汤米安吉洛接近崩溃的声音,他只好在电话里安慰他:“打起精神来,汤米。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现在想也没用了。这不是你的错。要怪就怪塞尔吉奥吧,他间接害死了那个女人。听我说,汤米,现在塞尔吉奥的运气已经用完了。”
汤米还在喘着气,他尽力从塞满了被炸弹炸死的女人的头脑中分析文尼的话,好不容易从牙缝里挤出了点东西,“你什么……什么意思?”他盯着梅赛德斯,嘴唇仍在以微小的幅度地哆嗦个不停。
“山姆和保利已经找到他了——他在镇子对面乔治餐厅里。现在你赶紧回酒馆一趟。”文森佐在电话里喊急了,电流声扰乱了他声音的细节,失真的信号声混杂着急切。
更多的人围在着火的车旁,有人打电话报了警。汤米仍在看那边,任由话筒从手中滑落,他勉强稳住身子,长长地呼出一口气。纯白色的梅塞德斯炸的只剩黑黢黢的框架,浓烟滚滚。街道远处有男人的呼喊,又有人走过去救倒在花丛里的老人,却被血肉飞的现场吓得晕了过去。
汤米·安吉洛最后看了一眼燃烧的车辆,开着自己的车子离开是非之地,从蓝色热带绕到失落天堂税务局,停在朱利亚尼大桥的下方,他本应该直接回到酒馆,但他觉得自己需要静一静,哪怕是一小会儿,虽然不愿意承认,但他被方才的事情吓得不轻,现在心里还有些发怵。随着车子的熄火,发动机逐渐冷却,车顶盖里面的发动机杆因为冷却一直发出类似于铁皮弯折的动静。他下车环视一圈,又盯着来时的路,确定没有人跟踪后,点了一只烟,沿着石台阶从小道走到河边,河边钉着矮石柱和铁链,他在河边站了很久,天色还未正式暗下来,但夜晚已在城市的街道间虎视眈眈。鸟群低飞在湖面。一辆白色的小型汽轮鸣笛驶过,水浪溢到石阶边缘。萨列里曾在去解决莫雷罗政府的支持者时跟他说:“这就是生意,汤米,因为某些原因,你喜欢上了鳄梨,你的邻居也喜欢上了鳄梨,大家都喜欢上了鳄梨,然后就会有人去做相关的生意,就有种种的帮派活动围绕着他们产生,这就是生意,这就是现代生活。”这段话是萨列里第一次试图,是一次提醒,更是一次测试,显然汤米·安吉洛通过了。自那之后他已经不再是个简单的司机,而是成为萨列里值得教导的可塑之才,直到现在。晋升是悲是喜以及人们口中的美国梦是否有实现他并不在意,心中的某种激情渐渐淡去了,这不是他想看到的,但托马斯·安吉洛无可奈何。上车后他打开电台,没有切频道,就这样听着重复了不知多少遍的格雷厄姆肥皂广告,沿着朱利亚尼大桥开往小意大利。
“看来塞尔吉奥比我想象的要难对付一些。”萨列里看着吧台桌上的地图和几张塞尔吉奥模糊的照片。
“保利和山姆也失败了吗?”
萨列里吐出烟圈,缓缓地说:“是的,保利在六点十几分的时候来电,说塞尔吉奥又一次逃了。”
汤米看了一眼手表,现在是六点二十五分。他又忘记酒馆的窗户早已被钉上,习惯性向外望去,只有密不透风的木板。他收回视线,轻轻咬住烟嘴,眯起眼睛去看桌上的照片。萨列里说着再次袭击的计划,按压着自己的眉骨。汤米拿掉嘴里的烟,用手指夹着,“当然了,一切听您指挥。”
“我希望第二天的上午就能看到好消息。”萨列里说完便站起来,“回去准备一下吧。”
萨列里上楼后,汤米也起身准备离开。
在一旁默默无言的文森佐突然站起来,用他那毛茸茸的手背摩挲着鼻子:“事情不是那么容易。”
“啊,是的,有点像咱们去年那段艰难的日子,但是……”汤米挑起眉毛,嘴角向下撇,“过去是只有咱们不好过,现在他们也得被搅进来。每个人都岌岌可危。”
“都会过去的。”
“但愿如此。”
“我们相信你,汤米。”文森佐走过来拍了拍汤米的大臂,笑着说,“有时候看到你,就像是看到我的弟弟。”
“谢谢你,文尼。”
文森佐笑嘻嘻地说:“早点回家,汤米。这段时间就别想着找妞了。”
“你这话留着给山姆听吧,失落天堂的花花公子。”汤米展露出笑颜。他握住文森佐的手,用力甩了甩,“明天见。”
“回见。”
与文森佐告别后,汤米开车前往母亲家。母亲和姐姐伊莎贝拉带着孩子早就搬到了新的居所,也在小意大利区,只不过与汤米的房子相距甚远。在丈夫戴维斯死后,伊莎贝拉并没有急着再婚,一个收入微薄的寡妇能养得起一个孩子,还住进了一间敞亮的屋子,很难不引起某些有心之人的注意。一九三四年的春天,有一个声称自己来自巴塞罗那的长腰长腿的男人试图追求伊莎贝拉,公寓所处街道的一家男士鞋店便是他名下为数不多的资产,可得知伊莎贝拉前夫的死因后,往日殷勤谄媚的男人变得对伊莎贝拉避之不及。伊莎贝拉和他谈起这件事时,脸上挂着不知道是可惜还是逃过一劫的兴奋。
他将车子停到了离她们公寓一条街以外的一个露天停车场,步行到了公寓。公寓的大门近在眼前,他那布满茧子的手碰到圆形的门扭,握住几秒后却松开,无力地垂到裤缝。他犹豫了许久,最终靠在小巧精致的双开木门的壁灯下,他压低帽檐,抿着嘴唇,紧盯着地面的裂缝,未干的水渍里倒映着天空。没人知道他那半分钟内想了什么,唯一知道的是他最终离开了门,向自己停车的地方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