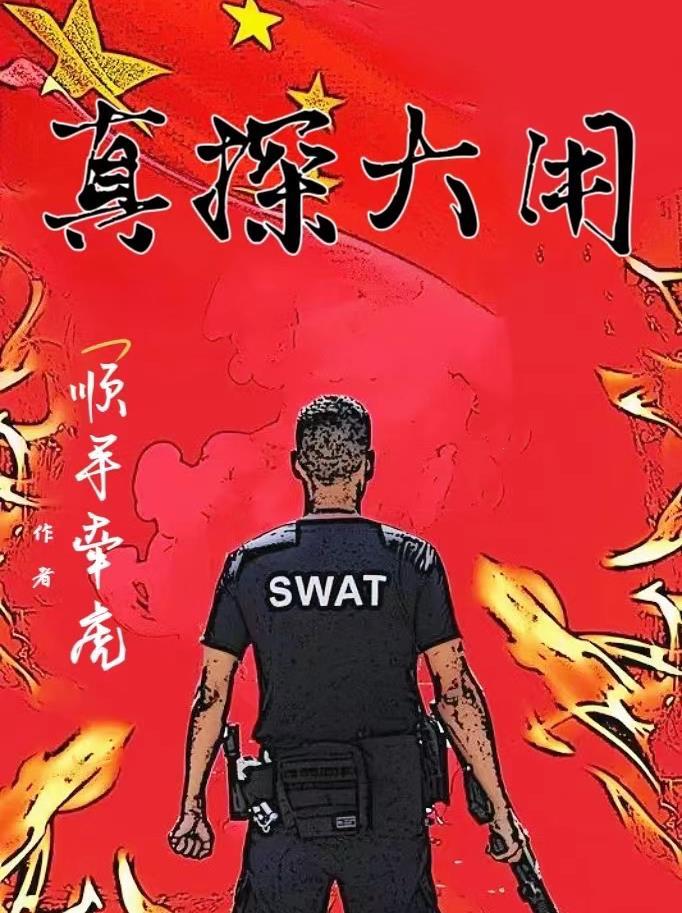笔趣小说>他是一个小结巴虞渊全文免费阅读 > 第47頁(第1页)
第47頁(第1页)
阮秋拿起刷子仔仔細細地刷著上面的泥沙,阿婆沒有在家,有可能是出去溜達或者是去看人打牌。筒子樓的一個死胡同里有一棵參天的榕樹,下面有許多乘涼的老人,三兩成群搖著扇子,聊天的下棋的,什麼都有。
阮秋還知道阿婆從那裡認識了筒子樓里的好些人,樓下阿姨的女兒才五六歲,也是由家裡的老人帶著,阿婆和她們能聊得起天。
阮秋對阿婆知道得太少太少,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阿婆不願意說。她並不是南方那座小城裡的土著,但從哪裡來,阿婆從來沒告訴過阮秋。
一會的功夫螃蟹就全被處理乾淨了。阮秋將自己早就準備好的黃酒拿出來,找了乾淨盆子一股腦倒了進去。
悶煮等待的時間是漫長的,阮秋搬了個小馬扎過來,安靜地坐著等了一會,奔波一天的勞累突然如潮水一般席捲全身。
有點困……
阮秋慢吞吞地給鍋定了時,自己則從廚房裡走出去,到自己的屋子裡準備小睡一會。只是剛閉上眼,許多事情便鋪天蓋地地壓上來,讓人直喘不過氣。
夢裡的畫面弔詭地呈現出單調的黑白兩色,猶如過期的膠捲在眼前單一地重複。
無數人的指責和陡然劇增的壓力,那台離自己很近的老式電話,那個猶如噩夢一般的電話鈴聲。
直到阮秋在夢中驚醒。
天色依然是亮著的,只是沒有睡著之前那樣亮。
阮秋以為自己睡了很久,但看了一眼時間,恍然發覺自己不過睡了十多分鐘。
但怎麼也睡不著了。阮秋只好站起身,慢吞吞地隨便找了個地方發呆。
他覺得自己也許是高興的。但是怎麼也高興不起來。
知道霍揚沒有女朋友時快樂好像只是短暫的,就像一劑興奮劑的針管刺入皮膚,那是短暫的興奮,整個人都似乎被無法抑制的情緒簇擁上了情緒的頂峰,但很快自己便摔下來了。
阮秋知道自己的反應好像總是慢一拍,好像從打不出電話、說不出聲音的那一天開始,他的人生、他的時間,便被一隻看不見的手按下了暫停鍵。於是他摔下來的過程也是很緩慢的,甚至更近似於一種緩慢的凌遲:從霍揚輕描淡寫談起省隊,再到許磊看向自己的那雙冰冷眼睛,阮秋不斷地在他們的情緒里掉落,從高山上跌落谷底,然後連骨頭都摔得粉碎。
他的血肉是一灘泥,骨頭碎片卻支棱著,是一片混亂的景。
潛意識裡的聲音告訴阮秋他真的做不到,可是他撿著破碎的自己,霍揚卻突然伸出一隻手來,幫他一起拼湊著那一具屍骨無存的人。
他說,你做得到。
阮秋抽了抽鼻子,遲鈍地覺得自己的感官在無限的思考里變得酸澀沉重。螃蟹的香氣在高度數酒的刺激下氣味更加香厚濃重,但似乎又將自己卷挾進另一段記憶里。這讓他眼睛有些發紅,把做好的醉蟹放進保鮮盒的動作都變得有些顫抖。
他重洗了一把臉,提著保溫盒,推著車子在筒子樓外的巷子口的便利店裡又買了一箱牛奶,朝著另一個方向開去。
*
楊驍開門的時候,他正頂著一頭亂糟糟的頭髮低頭打著遊戲,一臉不耐煩:「誰啊?」
阮秋有些侷促地站在門口,看見楊驍開了門,聽見他熟悉的聲音,鬆了口氣,提著牛奶和盛著醉蟹的保溫箱走進來。
玄關處亂糟糟的,阮秋記得自己上次來的時候也是這樣,他嘆了口氣,想從鞋櫃裡找出自己的拖鞋,楊驍頭也不抬地從同樣亂糟糟的沙發上說道:「你那雙都發霉了,早扔了。」
拖鞋長毛髮霉也像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只是那語氣里的不耐煩讓人有些刺耳。
阮秋看了一眼油膩膩的地,沒說什麼,先把醉蟹放到廚房的台子上,把那一箱牛奶儘量找了個乾淨的地方放下,又對著楊驍說道:「後、後天……」
楊驍依然是頭也不抬,但這次語氣明顯更惡劣了:「結巴,你能不能先閉嘴?我團戰快死了都。」
阮秋便沒再說話。
他去廚房裡找到了自己上次來買回來的百潔布,擠了一點洗潔精,端了盆水便走進一直關著門的雜物間。
牆上的遺像落著一層灰,供桌上也亂七八糟地擺了一團,楊驍看來是從來沒進過這裡。
阮秋先是打開屋裡的窗戶通風,先用干布擦拭了一遍桌子,又仔細地用百潔布擦著邊邊角角。
正當他跪下來擦桌腿的時候,阮秋聽到遊戲的聲音,接著又聽到楊驍那熟悉的滿是嘲諷的聲音:「結巴,你做這些給誰看呢?」
阮秋抿了下唇沒有說話,只是將髒了的布放在盆里洗了洗,接著繼續擦。
楊驍似乎是覺得沒,他盯著阮秋看了一會,又轉身去了廚房,很快就發現了多出來的牛奶和醉蟹,大驚小怪地拎著東西再次走進屋裡來:「又是牛奶?我說多少遍了這玩意我早就不愛喝了。」
阮秋沒有反駁,但他清晰地記得自己上來帶回的牛奶箱子已經不見了,楊驍早就喝完了。
「那是因為我扔了。」
楊驍像是看出了阮秋的心中所想,他滿臉嫌棄憎惡地看著阮秋,「你還不如買箱套回來呢。」
阮秋的臉色白了白:「下、下周你就高考了。」
「高考了才更要解壓啊。」楊驍無所謂地說道,「你幫我爹解壓過那麼多次,這種滋味你得比我更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