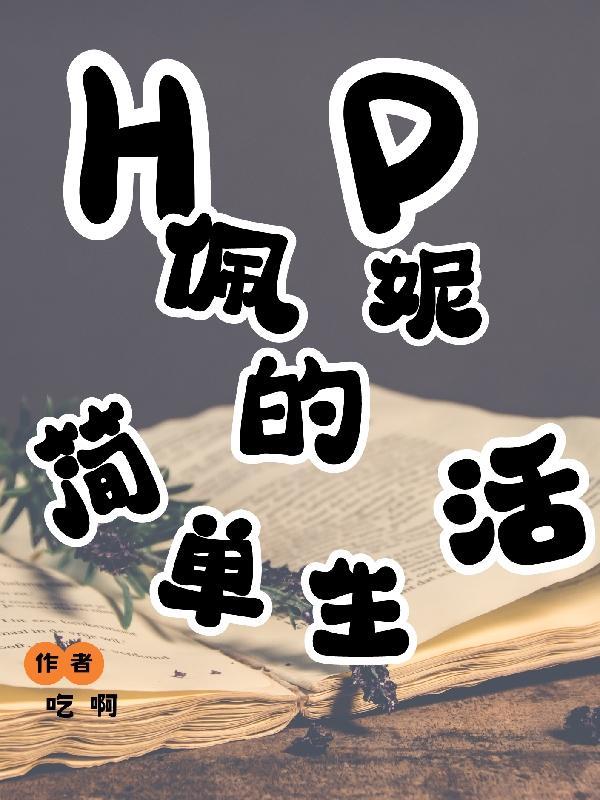笔趣小说>心机外室上位记讲的什么 > 去家庙(第2页)
去家庙(第2页)
他话虽说的冷硬,可心里忆起婉竹清瘦似素缟的沉静模样,忆起她那日俯在自己身下时潋滟着纯澈的明眸,以及那一句“我心悦世子爷”。
但凡他有一丝清明的神智在体,也知晓当时在那等境遇里,这外室是为求自保才会绞尽脑汁地编出了一句“心悦”来哄骗他,而非出自她真心。
她也许心悦自己,可心悦的定是他带来的权势与地位,而不是他这个人。
想清楚了这一点后,齐衡玉便竭力驱散了心内的惘思,只与静双说“退下吧。”
他端起茶盏,眼角的余光却瞥见了身形岿然不动的静双,“还有什么话要说”
静双鼓足了勇气,垂着头声音闷闷地说道“金玉遣人来给奴才送了信,说是婉竹姑娘这几日食欲不佳,还时常身子懒懒的。”
齐衡玉握着茶盏的手一顿,璨若曜石的眸子烁着些光亮,他凝望着静双,示意他继续往下说。
得了他的肯后,静双才道“奴才想,婉竹姑娘是不是怀上了身孕”
这几日雨雾不停。
婉竹将经书抄了一半,膝上跪着的蒲团沾染了水雾,跪久了只觉得浑身上下也染上了一股阴干的霉味。
金玉举着油灯入厢房,将容碧描到一半的花样子放在了袖袋里,见婉竹仍靠在迎枕上读着经书,免不了唠叨上一句“姑娘仔细眼睛。”
她也不知婉竹为何会对经书诗册如此敢兴趣,白日里跪着抄经书还不够,临睡前总还要捧着书读上一个时辰。
“今日镜音大师教了我几个字,总要好好写上几遍才能认个清楚才是。”婉竹说着已把眼前的经书阖起,见金玉鬓被雨雾淋湿,便去取了帕子来让她擦干。
金玉接过婉竹递来的软帕,脸上却有两分懊恼之意,“镜音大师是相国寺的高僧,谁曾想高僧也会怕这滂沱的大雨,竟还躲到我们家庙里来避雨了。”
“高僧也是人。”婉竹笑她,“怎么就不能避雨了”
主仆二人闲话两句,金玉湿了一半的也裹紧了帕子里,身子舒朗了之后她也终于有空说起了正事,“我将姑娘带在身上的银票都给了家庙里的这几个奴仆,他们按着姑娘说的话向静双递了信。”
做到这一步,若是世子爷仍不肯来家庙瞧婉竹,那便只能再想别的法子了。
金玉瞧了眼外头如墨色点漆般的夜色,心里隐隐有些失望。
这么晚了,世子爷应是不会来了。
呼啸的风声一阵阵刮过厢房的支摘窗,卷起震耳的声响,除了自然酿造的声响外,婉竹好似还听见了一阵断断续续的脚步声。
那脚步声只响起一瞬,紧贴在支摘窗这一头的窗棂里,婉竹霎时从炕上起身,肃着容问金玉,“白日里我让你拿来的东西呢”
金玉也脸色一白,霎时便伏下身子去拿桌案下头藏着的菜刀。
也正是在这时,天边的雨越下越大,盈灭嘈杂的雨声里裹挟着惊雷作响的声响。
婉竹的脸色愈难堪,攥着软帕的柔荑不断地收紧,掌心内也渗出了一层细汗。
她抖着身子与金玉一起退到了木床旁,那刀背着手而放,两人皆满眼戒备地望着支摘窗的方向。
这样的雨夜最益于杀人,不论流出多少血,也会被这磅礴大雨冲刷个干净。
齐衡玉推开家庙厢房屋门时,瞧见的便是这样怪异的一幕。
厢房内的烛火影影绰绰,光秃秃的陈设摆件遮挡不了他的视线,一进屋他便看见了躲在木床旁的婉竹与金玉。
这两人不知为何一齐靠在木床旁,清清瘦瘦拢在一块儿的一团确实有几分可怜的意味。
莫非又是这外室的苦肉计
他遥遥地立在离木床甚远的木架旁,盯着婉竹瞧了许久,蹙着眉宇问“静双说,你有了身孕”
插入书签请牢记收藏,&1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