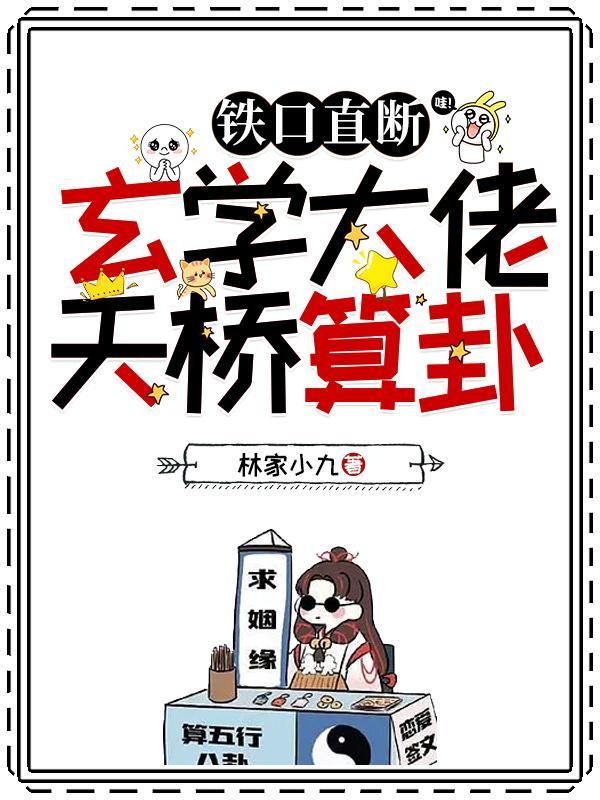笔趣小说>织魂引免费 > 第12章(第1页)
第12章(第1页)
久久无人回应,他只好抱着琵琶坐下来,开始演奏。刚弹出一个调,里头的人就打断了他,“渔阳参挝。”
听声音怪冷漠的,无忧应了声“是”,立马改换调子,奏起了渔阳参挝。
室内温暖生香,那曲调却仿佛风吹枯桑,悲凉而清越,寅月满饮了一盏又一盏,喝得眼前都有些重影了。
息市的街鼓响彻长安,一轮接一轮,天色已经黑透,黑得有些粘稠,然而长安真正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无忧弹了一遍又一遍,对面的客人没在宵禁之前离开,却也没有召他侍酒的意思。隔着纱帘,他偷偷打量她,心中暗叹真是个妙人,不收钱他也愿意。
终于按捺不住,他自作主张起身,掀帘过去倒酒布菜,拿腔拿调道,“客人是有什么心事么?怎地一人这样独饮?”
寅月终于肯施舍个眼神给他,却仍旧不语。
无忧面色窘迫,垂下头去,“奴貌丑无盐,想是惊扰了贵客。”
寅月恍若未闻,问:“你在南馆献艺几年了?”
无忧局促道:“有三载了。”
寅月道,“那么拘谨做什么?我又不吃人。”
无忧点头,欣喜道:“那入夜了,那奴伺候贵客更衣吧。”
“不必。”
无忧的脸立即垮了下去,但客人要走他也不能强留,又道:“无忧再替贵客抚上一曲如何?客人若是满意,还请时常来看无忧。”
寅月点头。
看他慇勤地穿过纱帘去弹琴,忽然被勾出了一些不好的回忆。从前她一定也露出过这样逢迎、谨慎的、讨好的神情。
骤然想起这些陈年往事,她倏然升起一种奇异的痛感,继而感到无边的厌烦。
这感觉就像撕开了结痂的伤口,伤口又开始流血、疼痛,但疼痛里还带着一些自毁般的快感。让人忍不住时时去揭开伤疤,饮下这些恨与快。
想到此处,她不由哂笑。
无忧见对面人的表情顷刻间变得阴戾癫狂,雅间内气氛诡异,弥漫着汹涌翻滚的杀意。
那只斜插着竹枝的细颈花瓶开始剧烈发抖,他吓得通体生寒,一时竟不知作何反应,只目不斜视地弹琴,以求放过。
寅月站起身,又恢复了那种近乎冷漠的神情,在胡案上放下赏钱,扬声道:“拿着赏钱快活几日。”
她还有绵长到接近永恒的寿数去修补这些痛楚,但这个乐人,却没几日可活了。
走出南馆,外间寒风刺骨。
寅月回身看了一眼南馆,其上妖气冲霄,灯火耀夜。里头除了那些寻欢作乐的贵妇是人,其余多数都是爬虫走兽、魃鬼饿鬼,将整座楼挤得满满当当。
再过一个时辰,就是猎血食的时间了。
而此刻,天幕上那顷刻间就要压断屋脊的乌云,就是这烟花地下的暗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