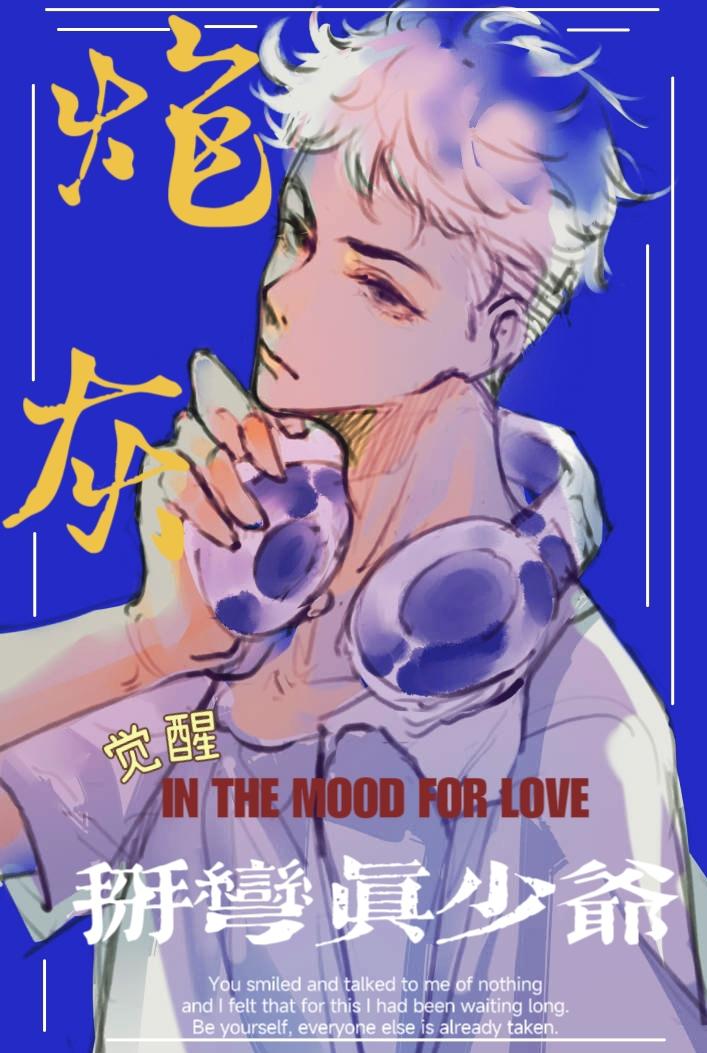笔趣小说>虫族之反祖 > 第19章 雌君(第1页)
第19章 雌君(第1页)
“笃笃。”
军雌低沉的声音隔着门板闷闷响起。
“阁下,请问我可以进去吗?”
费轶稍稍打起精神,他在沙上坐正,声音里没什么情绪:“请进。”
军雌轻手轻脚地推门进来,房门在他身后轻轻合上。
其实赛迦维斯也没想好要说什么。
他贫瘠的语言储备没办法让他像其他雌虫那样会哄虫开心。
他只能选择最直接的方式:“阁下,您看起来心情不好,是因为刚才那只雄虫吗?”
费轶没注意到元帅的用词变化,他抬眼,静静地看着赛迦维斯。
黑雄虫坐在暖色调的沙上,周围的光线与房间的陈设都是暖的,可雄虫像黑白色的剪影,怎么都融入不了这周遭的暖意。
赛迦维斯缓慢地踱步至他跟前,单膝蹲了下来。
他抬起头,与他的雄主对视。
“阁下,有些事实,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
元帅的声音带着沉沉的嗡鸣感,大提琴般缓慢优雅的格调,通过空气敲击着费轶的耳膜。
“这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不是没有虫试图改变、试图反抗过,但是结果都不算好。”
“您今天看到的,已经是比较温和的场面。”
赛迦维斯赤金色的眼瞳在昏黄的光线中泛着温暖的光泽,墨蓝色长披散在他肩背上,滑落了几缕。
费轶盯着他,不合时宜地想,元帅这个长相,放在娱乐圈绝对杀疯一片。
“现在阁下可以说说,为什么会不高兴吗?”
你和其他的雄虫是不一样的,对吧?
费轶的唇张合,声音像卡在了嗓子里。
黑雄虫突然笑了一下。
他弯起黑眸,仍是之前那一派温柔的模样。
“也还好吧,只是不习惯看到那种场面。”
赛迦维斯不知道该怎么描述这一瞬的心情。
好像是惊讶,又好像是早有预料。
或许还有一点说不清的遗憾。
他点点头:“原来如此。”
黑雄虫与军雌之间沉默了一会儿。
黑雄虫忽然叹了口气。
费轶声线柔和:“抱歉,我并没有想把负面情绪带给您,只是有些忍不住,”
他笑得眼尾扬起。
“侮辱刚成为雌君的军雌,这种行为应该受到惩罚吧?”
赛迦维斯愕然。
其实费轶更想直接说“去死”,但是觉得这样有些毁形象,所以他只是温温柔柔地换了个说法。
至于具体是什么惩罚,究竟会不会死,谁知道呢?
费轶虚伪地感叹了一声。
还是忍不了啊。
看到穿着军装的、应该站的端正的军人(或军雌)这样被一些垃圾羞辱,他这个火就噌噌地往上窜。
这会让他想起一些应该去死的垃圾。
赛迦维斯的心情像坐了过山车,突然俯冲又突然冲顶。
他扶了扶额,遮住眼里的一丝笑:“阁下觉得,应该要怎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