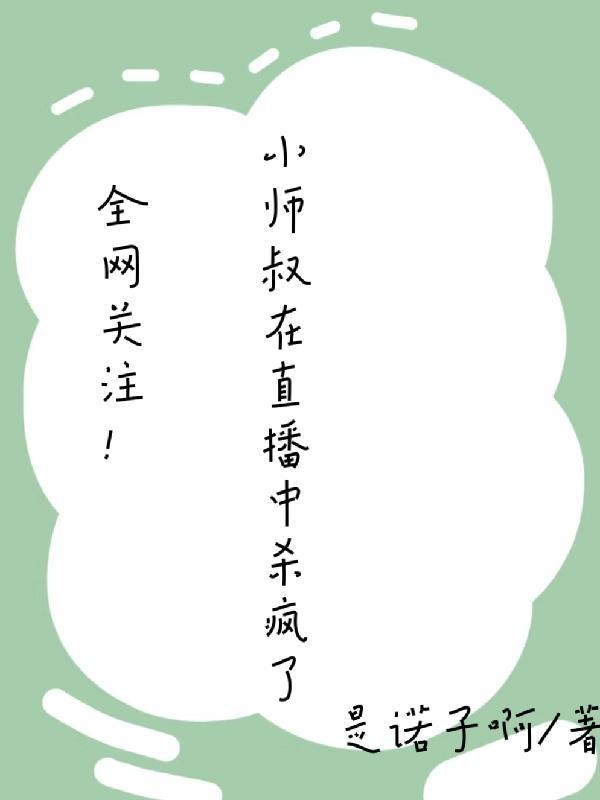笔趣小说>温带植物 雪碧 > 第82頁(第1页)
第82頁(第1页)
他知道就算告訴沈榆,這人大概也不會有什麼太大的波動,並對他的決定給予完全支持。
其中包括什麼都不說選擇隱瞞,以及讓他跟著上了自己的車。
插入車鑰匙的時候溫遇旬想,其實最好的解決辦法是不讓沈榆跟著,因為梁淑婷的人已經在路上,半路截車有不小的可能性。
她完全做得出來。
沈榆有時候太聽話太乖巧,讓溫遇旬覺得自己很混蛋,是在欺負人。
想了想不把人放在身邊他也不放心,邁巴赫高躥了出去。
上了回祖宅的高後沈榆仍沒說話,很專注地看窗外,心裡大概有疑惑,自己一個人思考得很認真。
他不問,溫遇旬只好主動說。
「我母親來找我。」
「嗯?」沈榆轉回來,視線落到溫遇旬有些用力握著方向盤從而暴起青筋和血管的手背。
「我應該沒跟你說過,梁淑婷是個瘋子。」溫遇旬陳述道,「是真的有精神病的那種瘋子。」
溫遠和她離婚的根本原因,溫遇旬不知道梁淑婷現在的丈夫吳家豪知不知道。
梁淑婷現在已經嫁入加多利山頂,做了富豪吳家豪的三房姨太。
可惜是不能再產子,大約就是因為這個才在吳宅受了委屈,嫁入吳家的這幾年,就一直沒停止過與溫遇旬的聯繫。
起先的電話溫遇旬還會接,但不可能滿足梁淑婷不經過大腦思考出來的要求,終於受不了一次一次電話騷擾,換了號,又與溫遠商量,溫家發力,壓得梁淑婷多年尋子無果。
梁淑婷走投無路,便只好求溫遇旬年少時的好玩伴段紹懷要聯繫方式。
段紹懷對朋友還是仗義居多,自然不可能給,但不知怎麼回事,原本在本家幫著父母收拾跨年的食材,梁淑婷的電話突然又打了進來。
准沒好事,段紹懷不打算接,但梁淑婷堅持,他不接就一直打。
父母側目,以為是他的露水情緣,段紹懷只好接。
「阿懷,」上世紀末的歌姬叫得段紹懷起雞皮疙瘩,「我現在到都了,他現在在工作的地方沒錯吧?」
「段紹懷剛才給我打了電話,說的就是這個事。」溫遇旬說著,餘光悄悄觀察沈榆的表情。
「我不想她找到我工作的地方去,所以先帶你回去,剩下的我來想辦法。」
沈榆手指蜷著放在腿上,表情鎮定,看著溫遇旬,過兩秒鐘眨一下。
看起來對溫遇旬完全信任,就算剛才他稍微提到了一下樑淑婷曾經做出的瘋狂舉動會真的傷到人,並和他分析了她半途追上來的可能。
沈榆靜了靜,說:「上次和你上。床的時候,我摸到了。」
「什麼?」溫遇旬一下沒懂。
「你背上的疤。」他直覺這疤與梁淑婷有關。
溫遇旬背上有道很長的疤,不知道怎麼來的,是沈榆在抱他的時候摸到的。
然而溫遇旬那塊疤痕似乎很敏感,和背上壘塊分明的肌肉相比摸著更柔軟,沈榆沒看到,但想像出來大概是只剩薄薄的、皺巴巴的一層皮包著肉。
說不清為什麼,但沈榆覺得溫遇旬這樣的少爺,要說受了什麼嚴重到留下那麼長一道疤的傷,應該曾經歷過一場重大的意外。
梁淑婷是溫遇旬童年最大的、最不穩定的意外。
溫遇旬沒什麼情緒地承認:「是她在我小時候拿燒紅的火柴劃的。」
究其原因也沒有別的:「她當時喝太多了,我去扶她,她以為我要和酒吧里的那些男人一樣輕薄她。」
沈榆覺得荒唐過頭:「……你當時幾歲?」
「十歲,」溫遇旬從小身量就高過其他同齡人,雖然存在一定認錯人的可能性,溫遇旬可憐她,但還是說,「我說了,她是瘋子。」
溫遇旬笑了一下,沈榆覺得他並不開心,像自我嘲笑,他不知道怎麼安慰,於是伸手摸了摸他緊繃的、冰涼的手背。
發現被跟車是在半路,沈榆是一直看著後視鏡發現有輛白色帕加尼不遠不近跟著。
窗外陽光很好,就算冬天沒什麼溫度,但明媚滿得從車窗外擠進來,光照到溫遇旬肩上,駁領處的胸花反光是再添的一把火,讓整個車廂空氣中漂浮的細小塵埃無所遁形。
「後面那個……」沈榆覺得自己疑神疑鬼,猜測的話只敢說一半。
溫遇旬食指在方向盤上點了兩下:「我知道,是她。」
在高上貿然停車是不理智的行為,溫遇旬知道梁淑婷既然已經找到他必然不會善罷甘休,他自己一個人倒是無所謂,但現在沈榆也在,於是車適中,算是默認了這場光明正大的跟蹤。
溫遇旬沒聯繫別人,但也不可能就這樣讓梁淑婷跟去溫家祖宅,下高後正思忖要怎麼解決,後頭的帕加尼就突然一個猛衝加,車身從邁巴赫的後視鏡擦過去,發出尖銳的摩擦聲。
這是一場緊急的逼停,溫遇旬如她所願猛踩剎車,臉色很難看。
所幸祖宅不在市區,這塊仍是偏僻,車停在路邊打了雙閃,過不多時,帕加尼上走下來一個中年男人。
溫遇旬面熟,那次梁淑婷給他在背上劃了長長一道口子的時候是他送溫遇旬去醫院,也看到過他深夜獨自進梁淑婷的臥室。
在香港半山大平層的孤獨夜景中,溫遇旬經常見到這個男人,卻一直不清楚他和梁淑婷具體是什麼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