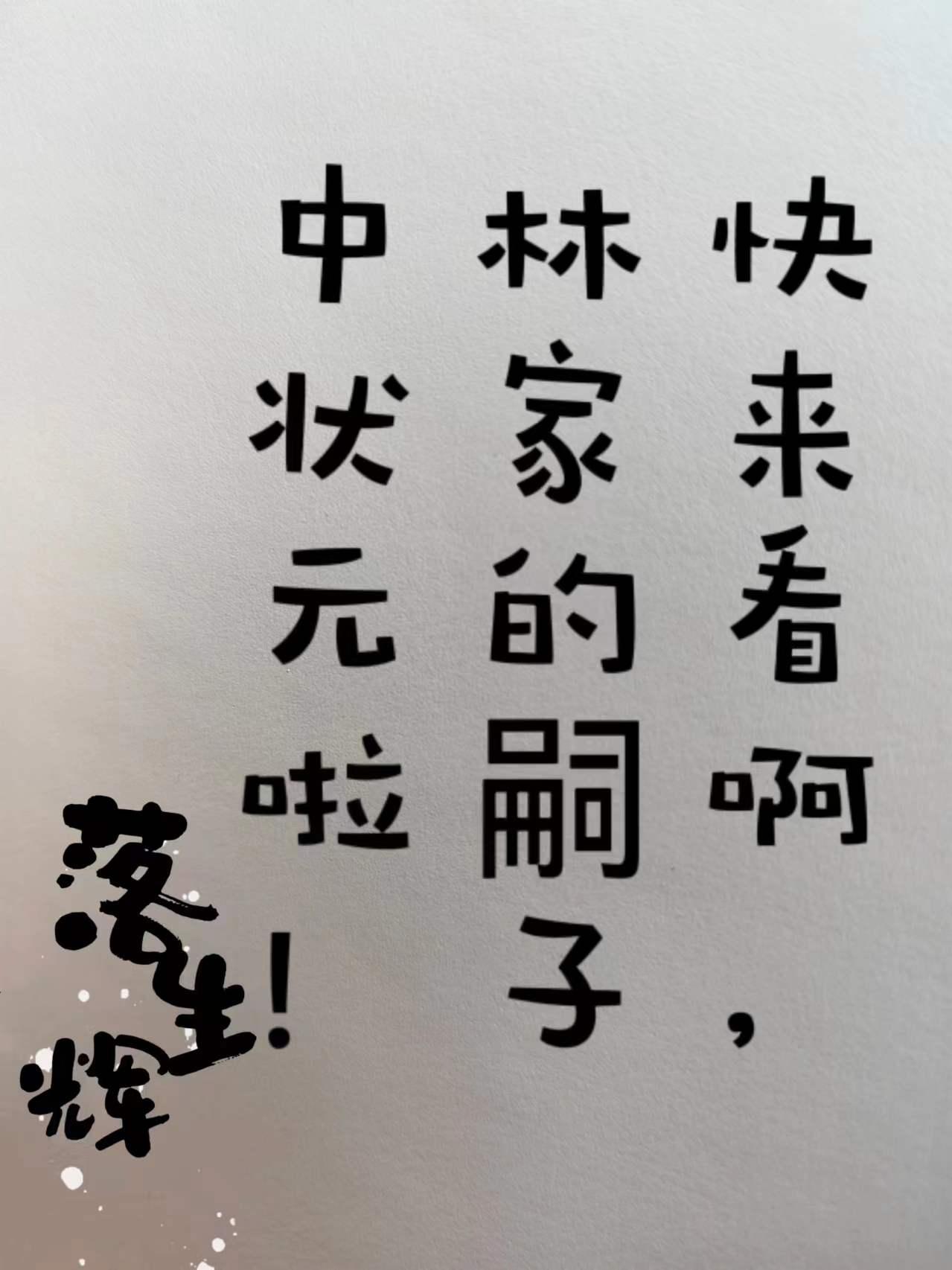笔趣小说>停电多久算事故 > 第33章(第1页)
第33章(第1页)
他的一只手正结结实实按在燕绥的胸肌上,手是从衣摆下方伸进去的。
言央鬼使神差地按了按,硬硬的,有些软,好熟悉的手感。
为什么?
燕绥任言央的手为所欲为,他早就习惯了。
那些他偷偷回来睡在人身边的夜晚,言央总会像这样把手从他睡衣衣摆处伸进去,在腹肌,胸肌上无意识似的摸摸按按,然后一脸满足地把脸贴过来,睡得香甜。
“怎么了?傻傻的。”燕绥问,看人撑在自己身上半天没反应,猜到人心里多半在琢磨什么,可他,并不想告诉他。
“没什么,你的腿?我有没有压到。”言央收回手,跪坐起来说。
“没有,你睡觉很乖。”燕绥睁着眼睛说瞎话。
言央睡觉,睡得死不说,整个人在床上简直可以三百六度旋转。
“燕绥。”言央气气地一声,知道燕绥是在取笑他,自己什么睡相,他活了二十九年能不清楚?
“好了,不逗你了,真没压到,我搭床外边的。”燕绥说。
一晚上……也不是晚上,大概凌晨五点到现在上午十一点,反正就床外边床边边轮流着放,不敢睡得太死,一是挂心着言央的烧退没退,一是配合言央千奇百怪的睡姿。
“今天晚上我去客房睡。”言央说。
“那我也去客房。”燕绥说。
“我怕压到你。”
“我会小心的。”
“你……”
“央央,你答应再不离开我的。”燕绥说着,伸手要抱人。
“燕绥。”言央依进燕绥怀里,“你变了。”
“没有。”燕绥说。
那该死的情感洁癖,让他在除了两人交欢之外,再说不出其他真心想说的话。
没有吗?言央想,或许是这样,变了的只是表现欲,以前的燕绥不会表现出来,言央也没有往这方面去领会。
比如吃鱼,燕绥会盯着鱼看,等着他发现他想吃鱼,然后主动给他剃了刺,放进他碗里,他才吃。
比如吃荷花酥,很掉渣的点心,燕绥常常掉得满身都是,要他给他换衣服。
比如咬过一口的芦笋,燕绥会嫌弃没有盐味儿,举到他嘴边,让他帮他吃掉。
比如把领带系歪,等着他发现,然后让他给他重新系一遍。
比如他换衣服时,燕绥会不声不响地站在他身后,等他转身时撞进他怀里。
还有,燕绥时常找不到袜子,内裤,衬衫,睡衣,这些明明都有分门别类,而且位置固定又明显。
一些不起眼的小小细节,突然像春雨一样密密绵绵地落入言央的心田。
“几点了?饿不饿,我去做饭。”言央说,情绪从柔软的心事里抽离出来。
“保姆在做,这几天你不用再做饭,等喉咙好了再说。”燕绥说。
“是以前的阿姨吗?”言央问。
“不是。”燕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