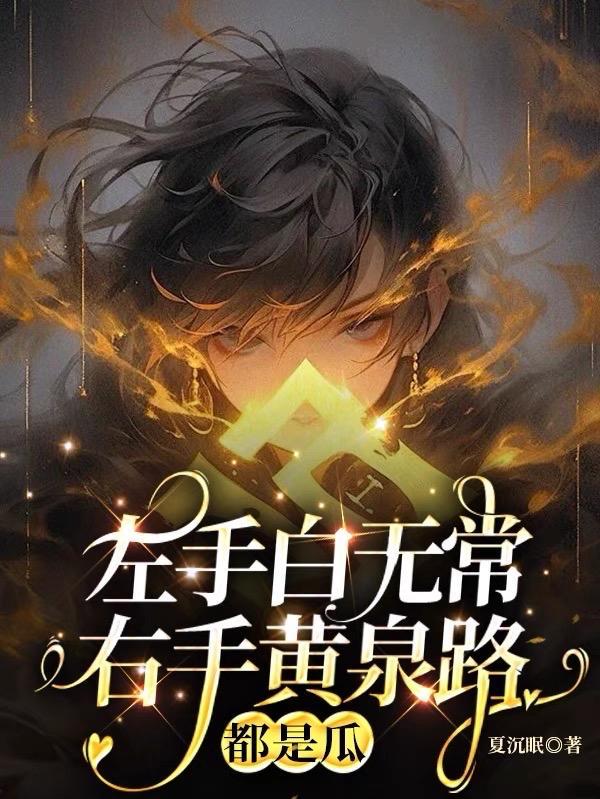笔趣小说>腹黑权臣受推荐 > 第108章 年少相伴的情意(第1页)
第108章 年少相伴的情意(第1页)
此后几日,苏檀一直在西苑吃药养着身子,十天后才勉强好了些,能出屋走走,只是面上仍旧没什么血色。
而年节即将过完,两日后就是元宵。
外头热闹喧天,隔着院墙都能听到苏府的喜庆,分明是在一个府内,这些热闹却半分都透不进西苑来,仿佛是两个世界,所有人都将大房遗忘似的。
除了苏璃月记挂着她,三夫人也派人送来了年礼,其他人都没动静,老夫人只让婆子送来了红封,里面的银钱连苏檀给采萱的压岁钱的一半都比不上,那婆子眼睛都飞到天上去了,送完后就飞快的跑,好似西苑多待半刻就沾染晦气似的。
采萱愤愤地朝那婆子的身影啐了一口:“呸!老贱人,那点儿银钱打谁呢!”
苏檀靠在圈椅上笑了笑,“看来二房是好事将近了,否则老夫人怎的连面子里子都不要了。”
“奴婢辰时听外头在传,说是二老爷升官了。”采萱撇撇嘴。
苏檀毫不意外。
也难怪老夫人现在恨不得将脑袋昂到天上去呢,原来是她最宝贵的二儿子又有出息了。
采萱还在骂着老夫人无耻,院门就被人敲响了,这回来的是苏璃月。
急匆匆进来后,她素来温和的面容此刻有些焦灼:“五弟,宫中有旨,宣你入宫一趟呢。”
苏檀微讶,挑了挑眉,见她气喘吁吁多半是跑着过来的,忙倒了杯茶递给她:“阿姊莫急,先饮口茶,是皇上还是太后召见我?”
大明的规矩,除了除夕元宵有宫宴会宴请朝中大臣及家眷入宫外,若非大事很少下旨召见人,此时还未到元宵,怎的这个时候宣她入宫?
苏璃月缓了口气,这才道:
“我同你细讲,今日我娘回外祖家,恰好我姨母也回了,上次我遭二房暗算那回,我姨母一直记挂着你的好,就透露了个消息,说是太后娘娘前几日过问了你的近况,她最是贪恋郎君美色,寻常时候哪会过问士族子弟,这回啊怕是对你起了心思,约莫是有意召你入宫侍奉身侧。。。”
听了这番话,苏檀嘴角抽了抽,不敢置信道:
“我与太后娘娘不过是一面之缘,时隔两三个月,她怎会还记得我?”
苏璃月翻了个白眼,“你还是纯粹了些,那太后娘娘年轻时就风流成性,能记挂你的美貌两个月也不稀奇。”
说着还压低了嗓音,接着道:“我听人说,她之前还是先皇妃子时,就与几个尚未完全去势的内侍有了尾,勾搭在一起,如今贵为太后更是不受拘束,随心所欲了,那些事儿都快摆在明面儿上了。”
苏檀的确是听说了一些,但万万没想到太后有朝一日会把毒手伸到自己身上。
难不成太后当真敢明目张胆地宣她进宫,再留在身边当面,不怕被外人知晓被人指责吗?
苏璃月问道:“你可知淮阴侯赵鹤?恐怕此次太后会假借他的名义召你入宫。”
“淮阴侯是何人?”苏檀对此人当真是不识。
“淮阴侯原是淮阴某地的士族郎君,一次偶然机会进宫赴宴,被太后惊为天人,深受其容貌吸引就设计弄到汴京,表面上封了个侯爵,其实背地里就是太后的入幕之宾。
而赵鹤至今都未婚配,不过是京中权贵高门都人尽皆知,谁会将自己的清白女儿嫁给这般人呢,否则有侯爵身份,其貌又不凡,怎会如今还是孤家寡人?”
说着说着苏璃月就意识到自己说远了,便叹了口气:
“总之五弟,你年龄还小性子又纯粹,怕是抵不过太后那深沉心思,我姨母将这消息道出来,是想让咱们提前想好应对之策,要不你暂时去庄子上避避风头?”
对于敦亲王妃的好意,苏檀心里很是感动,只是她转念一想,若是太后执意如此,人的执念是最为可怕的,越是得不到的便越会记挂在心,就算她避得了这次,那下次,下下次呢?
更何况,太后才起了这个心思,她就去了庄子,保不准太后会起疑,怪罪到敦亲王妃身上,苏檀也不想这般。
她思索了一番,摇了摇头道:
“阿姊,我知晓你和敦亲王妃都是好意,我亦十分感激,但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这件事儿还是要一劳永逸解决为好。”
苏璃月聪慧,觉得她说的有道理,无法反驳。
“阿姊放心,我心中已想好应对之法,只是时机未到,不好与阿姊讲出来。”苏檀安慰道。
苏璃月闻言,心下稍安。
自从上次祠堂一事,她便知晓五弟并不是如表面上看起来的弱小,而是有自己想法的,并非人人可欺。
还在她们三房无心永昌侯府侯爵之位,若是五弟能立起来,她们也是支持的。
聊到这里,苏璃月终于松了口气,又想到之前听过的八卦,便眉飞色舞起来:“五弟,我又得了个最新的消息,你想不想听听?”
苏檀笑着点头。
苏璃月兴致勃勃道:“你知晓为何长乐公主和督主这般亲密?原来当年督主开始入宫时,最先是在公主殿中伺候的,他二人从那时起便有年少相伴的情意,如今还是亲密如常,倒也不奇怪了。”
冷不防又听到萧时宴,苏檀就止不住皱眉。
好一个年少相伴的情意!
当真是好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