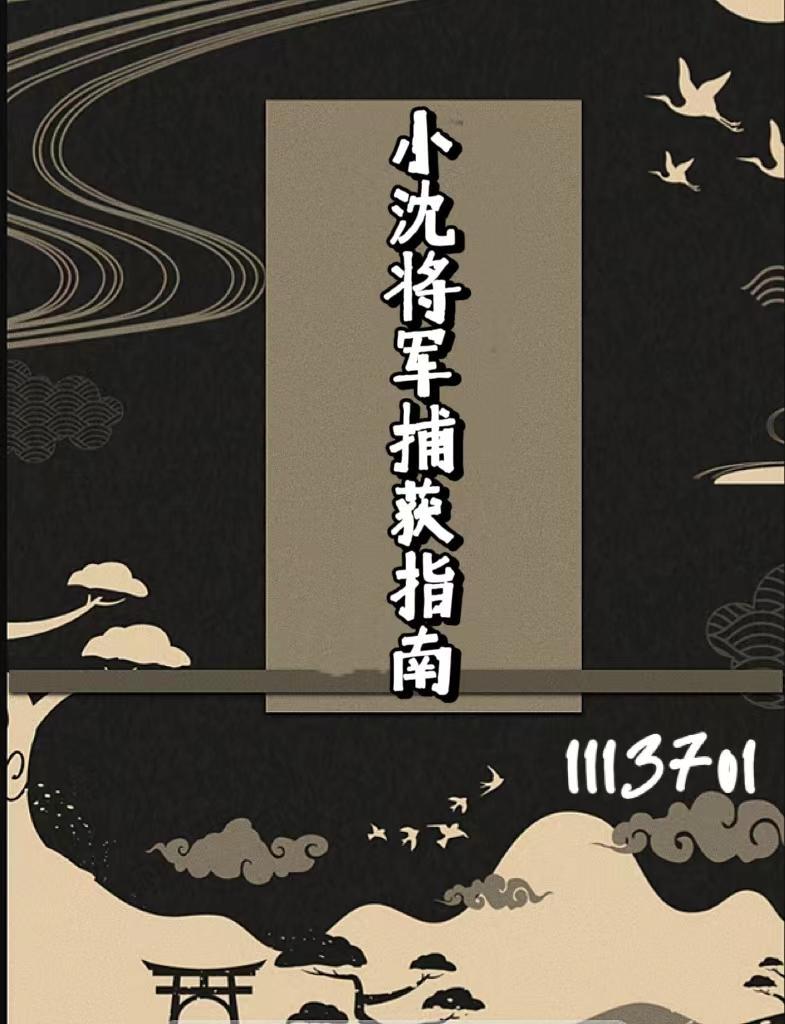笔趣小说>温带植物图片及名称 > 第56頁(第1页)
第56頁(第1页)
現在迫不得已要聯繫的時候不是沒有,電話號碼沈榆已經拿到了。
溫遇旬說:「不用,沒必要。」
要是沒有溫遇旬那晚在夢裡叫他名字的事情,沈榆就真像以前那樣縮回去了,然後在心裡對自己說「沒關係」、「再接再厲」、「我理虧他是大爺」。
沈榆手肘支在扶手盒上,撐著身體往溫遇旬那裡湊很近。
「哥哥,票都給你了。」
沈榆頂著他那張漂亮的臉湊過來本來就違規,容易透的、還沒幹的白襯衫貼在皮膚上露出上身肉體的顏色更是犯罪。
溫遇旬想起從前段紹懷喊他去吃飯結果是泡吧那次給他叫的女郎。
專業場所的氛圍怎麼著都比現在身體都舒展不開的車廂來得旖旎、繾綣,那女郎的長相確實是世俗意義上的無可挑剔,紅唇大波浪,靠近溫遇旬的姿勢和沈榆給他的感覺大差不差。
其實是差挺多,雖然目的可以算是一種類型,但沈榆一個男人怎麼都不像女人那樣婀娜,靠過來的時候也不扭屁股扭腰,僅看動作簡直有點正直。
那個女郎的手臂在碰到溫遇旬的一瞬間就被推開了,力度堪稱蠻暴。
段紹懷當時也沒想到溫遇旬會這麼大反應,笑得有些尷尬:「怎麼了旬仔,唔中意呀?」
他的語言系統一到內地就亂來,溫遇旬很久不在香港聽得挺變扭,冷言冷語的:「入鄉隨俗,別這樣叫我。」
段紹懷聽他的才有鬼,看著被甩地上趴著的女郎揮揮手讓她先走了,對溫遇旬說:「上次給你介紹了個漂亮小男孩你也說不喜歡,當時看到小榆講你原來喜歡男人你說只是喜歡他不是喜歡男人,現在又這樣……你好難搞喔。」
「你們不是都分手很久了咩?衰仔,我是掛住你嘛,怕你孤單寂寞。」
溫遇旬很沉默,他家是富但是家教嚴格,本身又是做科研的,更不願意在這樣的地方待著,一句話都不說只喝水。
看他這樣,段紹懷才恍然道:「你是還喜歡小榆?」
當時的承認有點不走心,也是為了不要段紹懷再給他出些么蛾子,罵人挺狠的:「是,所以你下次再搞這些就別活了,傻嗨。」
段紹懷還說了什麼沒想到他這樣的人原來這麼專情之類,他沒再聽完就走了,那個時候分手沒多久兩個人斷聯不見面自然能裝坦然,只是沒想到父母再婚把他們捆到一起後沈榆又在他眼皮子底下晃晃晃晃晃。
這下每天能看著,溫遇旬才意識到他心裡是真窩火,喜歡是真喜歡,恨是真恨,忘更是忘不掉。
不過沈榆靠近他,動作表情都沒有那種輕俗的媚態,看著更像撒嬌,又有一點害臊,死纏爛打的事情看來不常做還沒那麼熟練。
溫遇旬很清晰能感知到自己生理上的反應,但他這個人從來都對自己狠,知道自己不該要的時候就會瘋了一樣地抑制欲望。
狠慣了往往是能控制住的,只是他也是肉體凡胎,沒出家六根不算清淨,控制不住發泄的時候倒霉的是發泄對象。
沈榆拿票來說事,溫遇旬頂著一張冷臉從扶手凹槽把那票原封不動地掏出來。
然而沒還,只拿著在他面前晃了晃又收回去了。
「……」沈榆有點無奈,「你沒去聽啊?」
他唱之前還眯著眼睛在人群中找屬實自作多情,敢情人家根本沒來。
正要失魂落魄地坐回去之前卻靈光一閃,覺得不對。
溫遇旬的車沒停在停車場裡,現下車停的這塊地方是正對著舞台和觀眾席的公路,靠邊停,沈榆坐的副駕車門只能拉開一半,再多拉開一點會碰到樹枝和葉。
不是聾子不至於聽不見。
莫迪科音樂節本來就是一項很受大眾關注的演出活動,更別提這次還有電視節目加盟投資,於是安保力度搞得很足夠,演出外加觀眾和攝像機都需要場地,於是被劃出一大塊區域不允許車進入。
溫遇旬車停的前後都有零星幾部車,看著像劇組的。
就是不知道他怎麼能和劇組的車一起停在這裡。
「你的車怎麼停到這裡的?」
見沈榆緩過勁兒反應過來了,溫遇旬就沒多解釋,從剛剛放票的凹槽里又拎了個東西出來。
看著像個掛牌,一頭拴著繩子。沈榆覺得眼熟,多看了一眼就知道那是植培所的工作人員掛牌。
植培所在阿女山有長期的實驗項目,工作人員掛牌和通行證沒什麼兩樣。
走後門,有關係,好了不起。
不過既然聽到了,沈榆還是有說法:「那我都唱歌給你聽了,提個要求不過分吧?」
說得好像跟向他要溫家的公司股份似的,誰想得到沈榆就是在找溫遇旬要個私人微信。
沈榆的腦袋離他的側臉很近,溫遇旬一轉頭鼻尖就只對上幾厘米。
「你唱歌給我聽?」溫遇旬反問他,「這歌是唱給我的?」
又是抱怨騙雄黃酒又是以為來錯人間。沈榆面色微僵,決心改詞的時候他剛適應重生後的處境,在溫遇旬那裡受了軟硬不吃的打擊確實自己沒調整過來。
一腔怨懟全發泄到歌詞裡去了。
他現在說是也不行不是也不好,溫遇旬角度刁鑽,把他所有退路都堵死。
他好像很喜歡這樣,喜歡把人引入死胡同以後再掌控別人,滿足他的要求才親自指明一條生路讓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