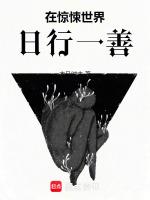笔趣小说>穿成寡夫郎之后全文在线阅读 > 第566頁(第1页)
第566頁(第1页)
這麼多銀子,林真想了想,跟家裡的顧尚書顧侯爺談起了生意,詢問朝廷有沒有意思修橋鋪路,他們林氏商行可以資助一些,叫百姓得些便利。
顧凜早就知道他對當今的路況十分不習慣,在離州還好,水泥路已經鋪得差不多了,走哪兒都方便。
但京都和其他地方一樣,只有最繁華的路段是石磚鋪的,其餘地方全是泥土路,天乾的時候塵土飛揚,下雨全是泥水,沒一塊兒乾淨的地方。
顧凜瞧著他,第二天就把摺子遞了上去。
他這個年紀輕輕的吏部尚書剛上任的時候,不是沒有人仗著年紀大,資歷老,想看他笑話。
小半年過去,那些人都老實了,都領略了這個二十歲的吏部尚書是個什麼樣的脾性,做事風格。
那就是一把殺人必見血的刀,能做事,敢做事,還深得皇上信任和重用,才剛上任那會兒就把推行了幾年都還沒推行開的堆肥法接到手上,處理了一批人砍了一批人,現在堆肥法已經深入到各州的郡縣,明年春天就要轟轟烈烈地用上。
對他的摺子,群臣們都豎著耳朵聽,深怕漏了一個字,沒一會兒,龍椅上的秦子文就對和林氏商行合作,一起修橋鋪路的事兒來了興致,叫工部和林氏商行接洽,看看此事的可行性。
這是一項利國利民的大事,凡是見過水泥的,誰看不出水泥的妙用。
於是在十一月,天氣已經冷下來的時候,朝廷突然廣發告示,徵發徭役,先從京都周邊開始,各郡縣修各郡縣的道路,先修主幹道,再修村路。
徵發的徭役有銀子,有吃食,雖然銀子不多,吃食也只是簡陋的餐飯,但畢竟是給自家修路,百姓的積極性很高。
林真算了算,等洛州那邊安遠鎮的路修好,應該要到明年去,以後就算不坐船,也能比以前縮短一半的路程了。
京都天氣寒冷,但到底不比離州,十一月只有薄薄的一場雪,將將能把屋頂蓋住。
生意步上正軌後,林真這個大老闆倒不怎麼忙了,跟下朝的顧凜不是在床上就是在床上。
又被逮著操練了一晚上,林真打著呵欠,聲音沙啞地道:「過兩天我想乘船回安遠鎮去,把阿爹阿父他們接來京都。」
「你政務繁忙,就不用跟著去了,一來一回也就一個月的功夫。」
顧凜抱著他的手臂收緊,臉貼著他的臉:「真真要把我丟在京都?」
林真把他退開些許,閉著眼睛嘟囔道:「我滿身的汗,你也不嫌棄,從前不是那麼愛潔的一個人。」
顧凜吸允著他的嘴唇,tian著他的唇齒:「真真是乾淨的。」
「毛病,」林真強行把他腦袋推開,揉著腫脹的唇,但是稍稍睜開些許眼睛,望著近在咫尺的臉,「哪是把你丟在京都,是去接阿爹阿父他們,你事兒多,我現在不忙,我去也是正常的。」
「放心,捨不得丟,你現在可是我的大靠山。」
「顧尚書,顧侯爺。」林真叫一聲親他一口。
突然,顧凜抱著他一個翻身,讓他趴在身上,黑沉沉的眼睛注視著他,手充滿意味性地落在他的腰臀上:「可是我還是不想去你去,你去了我怎麼辦,我吃不到你的嘴,舔不到你的xx。」
林真kua坐在他身上,兩人都沒穿衣裳,很快就能察覺到他的變化。
很快,顧凜的語氣變得沉甸甸的,又陰又冷,狂烈而躁動……
最終,林真還是能去安遠鎮了,不過每天都要寫信著人寄回來。
林真揉著自己的這把老腰,對這個結果還算滿意。
隨著兩人關係進展到現在,顧凜對他的占有欲越來越嚴重,甚至到了病態的地步,能去安遠鎮很是不容易了。
第三天,林真站在床前,展開雙臂,任由顧凜拿著衣裳往身上套,合上的衣領下面全是一片連著一片的紅痕和水跡,林真腦袋甚至有點暈乎乎的。
他望著正把披風披到自己身後的顧凜,語氣有些不岔:「你又這樣。」
顧凜將披風的綢帶打了個結,將披風的兜帽給他戴上。
兜帽上一圈雪白而又密實的皮毛襯得林真的臉又小又白,艷麗得驚人。
顧凜勾著唇,黑沉沉的神色很認真:「那真真在京都陪我吧,待我年底休沐,和你一同去安遠鎮。」
林真一拍腦門,就知道這小崽子根本沒打消過不讓自己去的念頭,他拉著顧凜的手轉身:「走,現在就走,下人都套好馬車了。」
開玩笑,再不走就走不了了,顧凜這小崽子從來不說假話。
身子還有些不適,但這麼久林真稍稍習慣了些,沒有一開始那麼難受,到動都動不了的地步。
他拉著顧凜,自己走在前頭,天空飄著細雪,宛如鹽粒一般。
一樣要跟著去的鹿鹿站在馬車旁邊,看見林真和顧凜一前一後出來,連忙把腳凳放到馬車旁邊。
林真站在院子大門外,鬆開顧凜的手,站在馬車前望著他道:「你放心,我很快就回來,跟著阿爹阿父他們一起回來跟你過年。」
「嗯。」在外人面前,顧凜永遠是那副冷淡到寡情的模樣,叫人瞧著就不由自主地繃緊了後背的皮。
隨行的下人們大氣都不敢出,微微低著頭。
林真看他崩著臉的樣子,突然挨近他,踮起腳尖在他唇上親了一口,然後踩上腳凳登上馬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