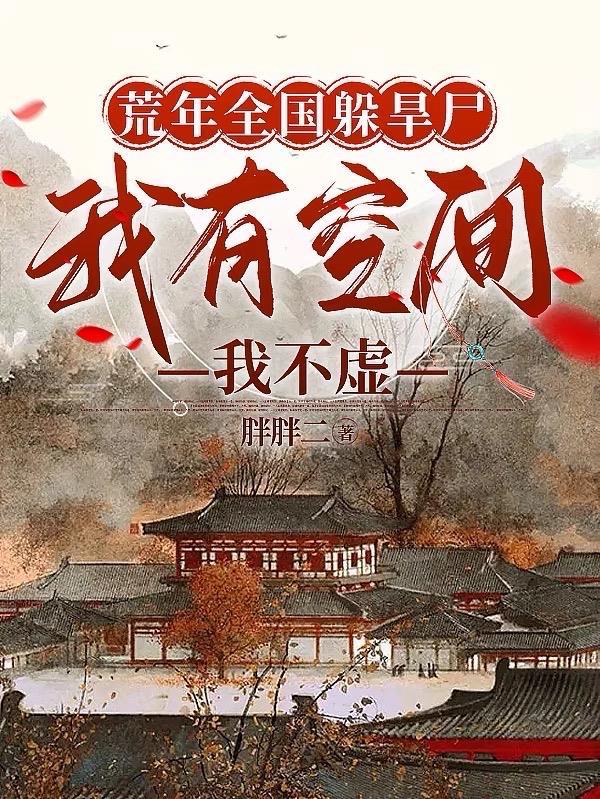笔趣小说>通房生存手册梨鼓笙笙 > 第092章成名(第2页)
第092章成名(第2页)
曼曼的日子一如从前,她除了给陈云端打打下手,算算帐,多少也算长了些见识,有意无意的便也打听些出府之后的事宜。
陈云端倒也没瞒着,直言道“只要你拿了卖身契,留下也好,出去也罢,一切随你意愿,老爷和太太不会过于为难你,陈家一向也算善之家,你与小六儿又并没有实至名归”
曼曼犹豫了半天才问“那个,不是说,还有婚书之类的,该如何销毁”
陈云端愕然了一会,毫不掩饰的笑道“没有婚书。”
他想起陈云正吓唬苏曼曼的那番话来,没想到隔了这么久,她还信以为真,瞧她那惶恐的模样,只怕这些日子以来没少为这件事纠结吧。
曼曼气红了脸,在心底把陈云正骂了个狗血喷头,他那么小竟然敢骗自己,真不是个东西。但没有婚书这玩意,她也就轻松多了,只要她能攒够二十五两赎身的银子。
曼曼所有的人生目标就只剩下了这一个,她要攒钱,她要为出府而努力。
陈云正这一走就是半年。
每个月都有书信来,是直接送到陈云端手里的。别人只当他们兄弟感情好,也只有陈云端知道这位六弟的心思。
每每家中上下阅遍了陈云正的书信,陈云端便交到曼曼跟前,道“你给六弟写封回信。”
陈云正的书信渐渐自成风格,时常说些出外游学时的风景、民俗、趣事,再就是说些自己的生活琐事,文风诙谐,用辞简练,难得的竟有一股洒然飘逸之风。
曼曼难免要掠上几眼,竟有身临其境之感。
但她不傻,让她代笔可以,可让她代写回信,门儿都没有。她铺好了笔墨纸砚,定然十分郑重的坐到陈云端对面,道“奴婢准备就绪,大爷请吩咐,奴婢也好给六爷回信,免得他在外思家心切,多有惦念。”
总之他不说,她就不写,曼曼严格把自己定位在代写书信的先生之上。
曼曼基本上忠于陈云端的口述,不加一点主观、感情,写完了还要给陈云端过目,态度十分之谨慎,生怕会把她扯进去一分一毫。
陈云端同李氏说起,道“我如今是真的看不明白了,小六儿他们俩这是要闹哪样”
李氏对曼曼虽然并未完全去除戒备之心,但有茶浓不住的在一旁劝着,又有春纤、水纹等人在陈云端身边严防死守,她也勉强安了些心,况且她再度被诊出了喜脉,又没有多事的徐妈妈在一旁阻隔他们夫妻相聚,陈云端又时常肯同她说些私密话,心胸倒不似从前那狭獈,还能说笑“六弟要闹哪样,只有等你亲自问了他才知晓,只是就他那傲气的小性子,只怕闷在心里了霉他也不会吭一声儿吧。”
陈云正对苏曼曼执念之深,让李氏感佩,同时也替他叹息。不是苏曼曼多不好,而是她那样的身份,注定是不可能跟陈云正在一起的,陈云正迫不及待的想要长大,表现出他的能力,可越是这样,越会让他们两个越来越远。
陈云正却没有什么表示,仍然按步就般的每月一封家书,就仿佛毫不知情是曼曼代笔,书信的口气也越随意,不似诚惶诚恐的向父母兄长禀报,而有点像夫妻间的喋喋絮语。
这一去,就是三年。
对于曼曼来说,这三年没有什么可值得称道的大事。生活总是有小矛盾、小争执,也总是有明争暗斗,冷嘲热讽,但都伤不到她的筋骨。
如果非得说有什么事的话,那就是她的初潮终于来了。
赎身的银子也攒够了,她有些雀跃的等着三年期满。
还有就是,陈云正以十一岁的年纪,考中了秀才,这几乎全县为之轰动的大事,陈家更是连放了几天的鞭炮,摆了十几天的流水席,陈老爷乐的合不拢嘴,把县上所有稍微有头有脸的人都让回陈府奉为座上宾。
但陈云正没回家,即使他几乎成了全县读书人的荣耀和榜样,可他没有一点得意和骄矜的意思。从书信里得知,他和几位同窗去了京城,自然还是打着游学的旗号。横竖他不缺银子,又不必侍奉父母,倒也游哉悠哉。
曼曼有一种“吾家有弟初长成”的欣慰。当然她也不过就是那么随意一想罢了,附赠着对他绝对的祝福和对自己绝对的自嘲。
她绝对不会把陈云正的上进归为自己功劳,也不会对她和他的未来报什么期许,只不过,毕竟曾经相识一场,得知他平步青云,越来越好,总比听说他失意落魄要好的多。请牢记收藏,&1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