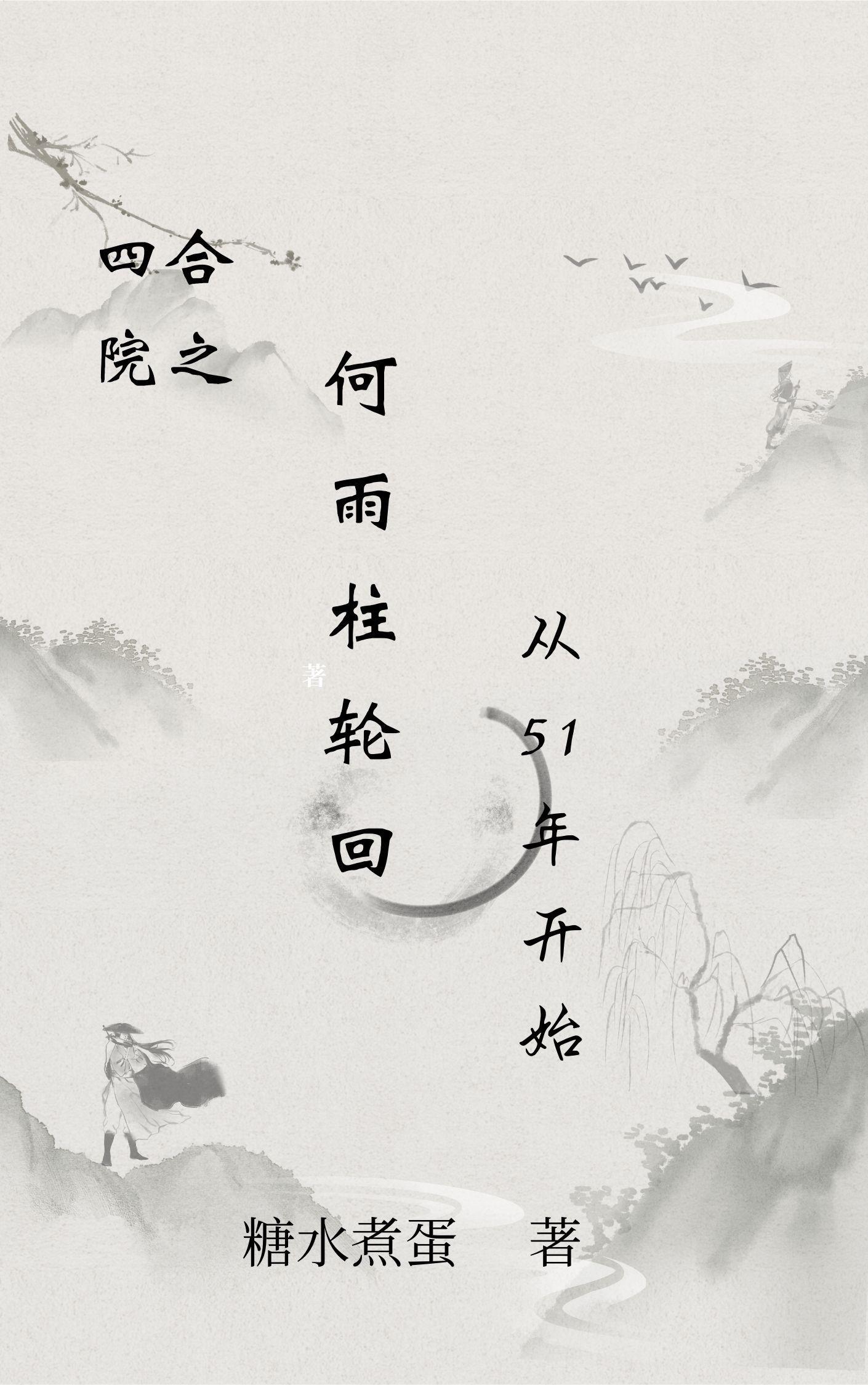笔趣小说>娇气包假少爷求生指南笔趣阁 > 第94章(第2页)
第94章(第2页)
白初贺“嗯”了一声。
站在和记忆里如出一辙的地方,身旁人叫他时,他以为会是一句熟悉的“狗儿”,但传到耳中的却是“初贺”二字。
他已经习惯这个名字很多年了,但此刻却不可控制地感到陌生,陌生到他没有张口回应。
转头的时候,一瞬间,他以为自己会看到一个十来岁的精明男生,但最后,映入眼帘的是已经成人,沉稳了不少的壮实男性。
大庆大概能察觉到一些白初贺的情绪,他没说什么,指着地图又说了一句,“狗儿,咱们往哪儿走?”
“初贺还能记得?”牧枚有点惊讶。
大庆呲牙直乐,“他以前教小月亮背了好几遍火车站的路线,怎么走往哪儿走,估计都刻进骨头里了。”
牧枚也忍不住跟着乐,“真的啊,怎么教的啊?”
白初贺终于张口,一双睡凤眼斜瞟了一眼大庆,“东门进来,左转下楼去地下一层,再往前走。”
大庆嘿嘿笑了好几声,“行嘞,走吧。”
白初贺走在前面,大庆和牧枚跟在后面,牧枚还在想大庆刚才说的那句话,“大庆哥,还没告诉我呢,初贺怎么教的?”
大庆又嘿嘿笑了起来,“怎么没告诉你,不是告诉你了吗?”
“哪儿告诉我了?什么都没”牧枚忽然反应了过来,也忍不住笑了,“晕,不会就是刚才那句吧?”
“对啊。”大庆乐得露出一口小白牙,“就是这么教的。”
牧枚一边觉得好玩,一边又忍不住压低声音问,“为什么教小月亮这个,怕他走丢吗?”
“嗯。”大庆的声音也压得很低,“火车站人多,怕小月亮万一走散了找不到站。”
牧枚闻言,心里也挺不是滋味。
不知道小月亮最后有没有找对站。
他们三人,大庆是经常挤火车的,白初贺也算是有点经验,反倒是牧枚很少坐过火车,许多流程都搞不太懂,只能在后面跟着他们两个人。
海市到南市不算远,大约两个多三个小时的车程,买卧铺实在没必要,他们买的是硬座票。
进站检票的乘务员是位中年女性,看见队伍里有个花臂纹身带两个学生的壮实男子,心里不由得警惕,检票时检查的很仔细认真。
检查白初贺的身份证时,乘务员放行前忍不住多看了两眼,等白初贺登上火车后又忍不住回头看了一下。
检完票,另一位地勤过来闲聊,开玩笑道:“咋了李姐,给你女儿相看男朋友呢?”
被称呼为李姐的乘务员忍不住白了他一眼,“咋可能,我是觉得刚才那个男生看着有点眼熟,才多看了两眼。”
“眼熟?”那位地勤不怎么在意,“咱们这儿天天人来人往的,有两个长得像觉得眼熟的也正常。”
他说完,去另一边巡视去了。
“那也不能同一趟火车一下检到两个眼熟的吧。”乘务员在原地确认好时刻表,咕哝了一句,转身上了车。
白初贺他们的车次靠前,放下行李后,牧枚说要去后面买点水,白初贺和大庆先坐下。
火车还是老式的绿皮火车,车上仍旧乱哄哄的,充斥着南腔北调,香烟混着泡面的味道,和从前别无二致。
“外面看着人少,其实坐车的人还是挺多的。”大庆感慨了一句。
白初贺盯着圆角的方窗外,强迫自己不要产生多余的情绪,听着大庆的话点了点头。
窗外,绿皮列车的边上,乘务员脖子上挂着金属哨子,低头在填表。
一切都和过去很相似,白初贺甚至觉得那位乘务员的背影看起来似乎也和十几年前为他们检票的乘务员十分相像。
乘务员转身上车了,白初贺才回头,看见牧枚已经回来了,手里拿了三瓶可乐,叮铃桄榔地放在桌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