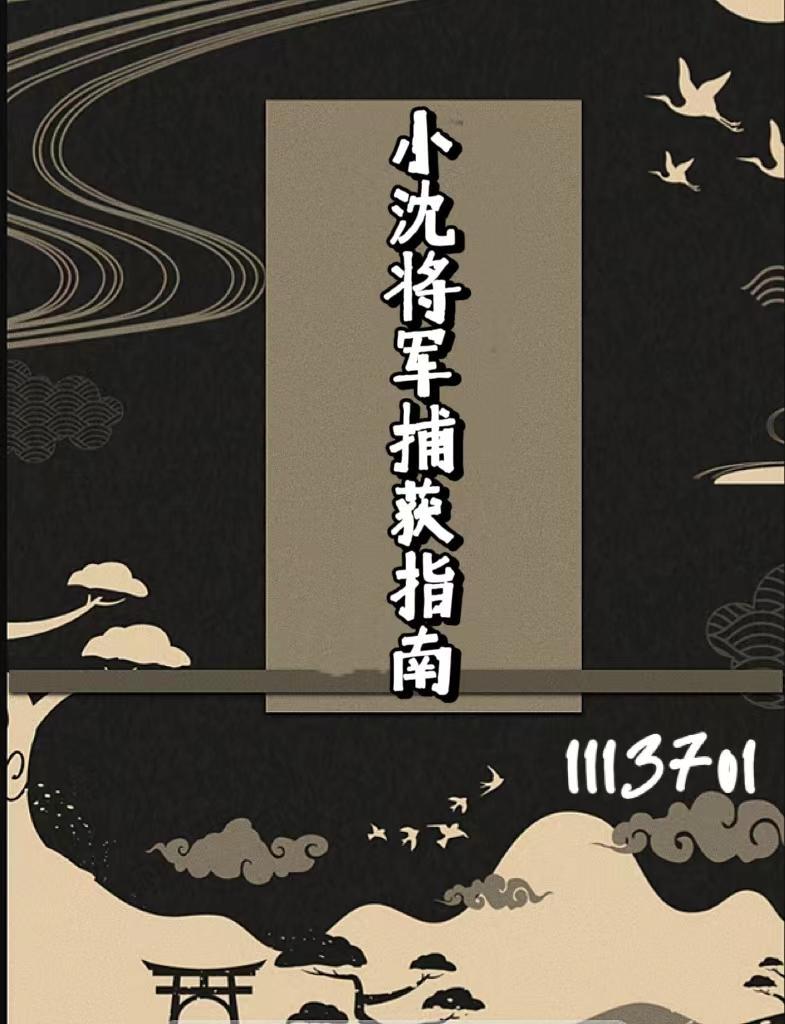笔趣小说>暧昧备份笔趣阁 > 第40章(第2页)
第40章(第2页)
孟醒被她拽得往前走,简芮希在他前面头也不回地说:“我们来这里这么久,你应该也有感觉到吧。”
“什么?”
“我初中的时候寻过死,割过腕,父母不理解我为什么会得病,只是觉得我矫情,说他们那个时候根本没有心理疾病这种东西,说我就是活得太好才会得这种闲病。好不容易答应我去看一次医生,又在医生面前对我冷嘲热讽。”
可是香格里拉的每一片云、每一阵风都来自最纯粹的凭空出现,常常由最浓重的蓝白绿组成,世界就剩下了三种颜色。寺庙香火不断,每天有人献上最纯粹的跪拜,和最热烈的经幡,好像真的所有心愿都可以实现,这里又不会辜负信仰,当天太高的时候,人就只是一颗微小的杂质,一个关于存在意义的命题。
简芮希不是一直待在房间里打游戏,她无法描述自己第一次见到日照金山时刻的感觉。
不同于孟醒心里浩瀚的沉静,她确实哭了,没有缘由。
要是一定要说,那应该是生命力、爱,和太澎湃的自由。
可是这些她说不出来,无法描述,只好对孟醒眨眨眼:“可是你也知道的,香格里拉是会让希望重新滋生的地方。”
“毕竟你看江措的眼神,哎呦,”简芮希揶揄道,“你怎么那么喜欢他。”
孟醒走后不久,五分钟,江措也跟着下了楼。
他来回过不少次事务所到民宿的路途,已经不用谁再带着他走,于是出于一些自己都不知道的原因,他选择跟了上去。
他一直保持不远不近又不至于被现的距离,像一个真正的路人,以旁观者的视角紧盯着孟醒。
是我和他在一起太长时间所以太了解他,才导致他出现一点情绪的低落都觉得地动山摇了吗?
孟醒的那个朋友和他一路走,好像也没多大现孟醒不对劲,江措面无表情地把手放在上衣口袋里,觉得自己有病。
有什么好跟的,自欺欺人。他看着孟醒,现自己完全没有办法把自己抽离成旁观者。
江措很久不抽烟了,在看孟醒经过斑马线的时候点了一支。
快要到事务所,走完这个斑马线就是,他不打算再跟着了。
他正要走,突然看见那两个人不走了,然后孟醒说了句话,简芮希的表情有一瞬间很促狭的变化,但很快又恢复成平时的样子,再变成一种很幸福的笑,最后……
最后握上了孟醒的手腕,江措咬了一下烟嘴。
孟醒好像真的不太会和女孩子相处,简芮希又转头对他说了些什么,这下促狭的人变成他,耳朵都红透了,和耳垂上的耳坠形成两极的色差,像个麻袋一样被简芮希拽进事务所大门。
有这么害羞吗,江措又咬了一下烟嘴,轻蔑地哼了声,眼神是自己都意识不到的刻薄的讥讽。
不过是被牵一下手而已。没出息。也不见得和自己牵手的时候害羞过。
尾随行动结束后,江措去了前段时间帮忙修冰箱的家电铺,老板看到他来赶紧站起来,和他诉苦说最近店里人手不够用,那个小学徒学得又不好,现在还只能打打下手。
看到那个小学徒正对着两截不锈钢材料愁,他抬头就看到江措:“阿措哥哥!”
江措把外套脱了绑在腰上,背心露出两条手臂,其中一条还缠着绷带,“嘴这么甜,难做的又要给我?”
但还是带上手套接过了焊枪和护目镜。
他不知道简芮希和孟醒说了什么,只是确实产生了一点好奇心。
反正他能承认的就只有一点。
“阿措哥哥你吃水果吗?”小学徒很殷勤地递来一碗老板给的仙人掌果。
“不吃,离远点。”江措在忙,伸手挡了他一下,不让溅出来的火星碰到他。
小学徒愣了一下,抱着碗边走边嘟哝:“不吃就不吃嘛,奇奇怪怪的,凶我干什么……”
江措抬起头隔着护目镜看他,举着通电的焊枪笑了声:“你说什么?”
“没有!”
下午江措突然接到孟醒的消息,问他还有没有在民宿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