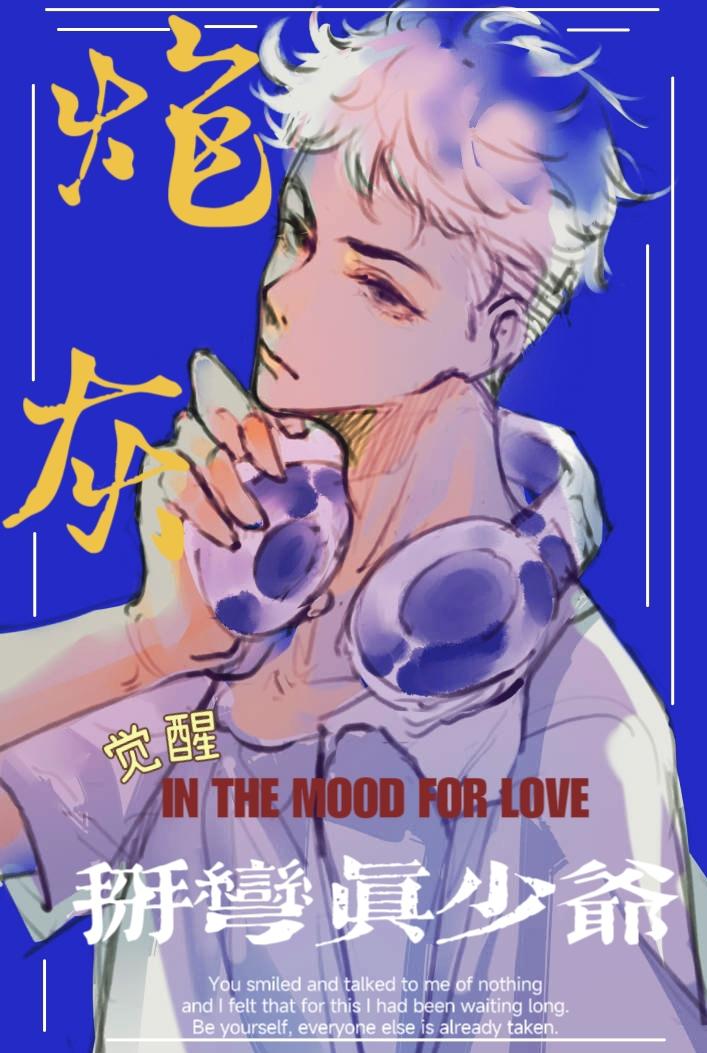笔趣小说>奴婢是王的侍妾 > 第二十一章 恶劣修15(第2页)
第二十一章 恶劣修15(第2页)
齐暄摇头:“孤虽不喜,但孤不想你离去。”
楼信喉头一哽,古怪道:“奴不会离开。”
齐暄显然不信,声音轻缓:“好啊,那信信证明给孤看。”
他操纵灵力,召来根又短又细的琉璃棒,棒尾有红线。
楼信在他接连不断的花样玩弄下,立刻猜到他想做什么。
在楼信惊恐的神情中,齐暄轻轻笑道:“孤给你两息的时间,信信无论尿多少,孤都会堵住信信的延孔一整天。”
楼信屈辱阖眸,他真是栽在齐暄身上了,连这么过分的玩法都愿意。
前端延孔早已有热意涌到附近,楼信用了灵力推助,延孔淅淅沥沥漏出透明无味的热液,濡湿了他身下锦被。
尝到泄尿的快感后,延孔水流如注,哒哒淌透三层锦被,从臀部到大腿,身下一阵温热。
他总算赶在两息之前,泄完了一次,就是躺在湿热的锦被上,未免难受。
齐暄欣赏完他躺在锦被上泄尿的全程,觉得很是有趣,控制楼信排泄的体验新奇非常,就像楼信是个任由他操纵的傀儡偶玩具,完全属于他,只为取悦他而生,这个认知令他难过又满足。
沈长欢说爱是成全,但估计他这辈子都和这词沾不了边。
不过没关系,他很喜欢楼信就足够了。
正如现在,他趁着延孔被尿液冲开的洞口,塞进去那根琉璃棒。
窄小孔洞艰难吃进去琉璃棒,冰冷光滑的棒体撑开里面的软肉,绞得楼信又冷又疼,难受的紧。
自己躺在自己的尿液当中,楼信感到淡淡的恶心和羞耻,秾丽五官沾染些许难堪与欲色。
他竟然是用女穴的尿孔排泄,真当了身娇体软的双儿不成?
照这样下去,齐暄不仅不可能像话本中那样厌弃他,反而对他的身体显露出相当的恶趣味,感兴趣到想彻底掌控自己。
楼信忽然有点后悔今生这么早认定这个人,他以前怎么没发现齐暄还是个变态,太……
他为什么要一时脑热表露心意,把人惯得这么有恃无恐。
照这样下去,他迟早会被齐暄在床榻上弄出病来,虽说他愿意被齐暄玩,但他目前只能接受被齐暄打,被齐暄肏弄,还有一些常见的道具玩弄。
至于按照齐暄命令,随地尿出来,他暂时有点接受无能,但联想到他上辈子做了什么,他权当以身抵债了。
这辈子他全心全意喜欢齐暄,愿意接受齐暄这些癖好,对方真是赚大发了。
这边齐暄欣赏了一会儿他躺在锦被间茫然失神的模样,才伸手解开他四肢的锁链,楼信生得白,这几个地方因挣扎磨出红痕,还好没磨破。
楼信刚一解脱出来,活动下手脚后便离开了那处湿透的锦被。
齐暄不知道从哪搞来的黑色长巾,他刚站到地上,就被裹了个严严实实,仅露出臂膀和小腿,还系了个结,牵扯到乳夹,有点疼。
楼信看清是什么颜色,诚恳谏言道:“陛下,后妃不能穿玄色。臣今早那件青色衣衫应当还可以穿。”
大胤有品级的官员和帝王才能穿黑色。
碰巧楼信这两点都不占。
齐暄吻了吻他的两瓣薄唇,沉声道:“孤说你用得你便能用。至于那套完好的衣衫,你不必穿,穿了也要脱掉,反倒碍事。”
规矩都是人定的,他不排斥楼信参与政事,等调查清楚后他也不可能完全把人圈在后宫。
何况大婚前日,他心中有怨,没给人备正红色的嫁衣。
只能以后再补楼信一场封后大典。
但最近几天,沈长欢回来前,楼信都别想碰正常衣服,侍奴的常服必须暴露易脱,将淫靡的身体展现人前。
楼信摸了摸齐暄吻过的地方,听到他的话面上发热,诧异道:“陛下这是要做什么?”又是不准他穿正常衣服,又裹住了他身上的几处隐秘。
齐暄淡然道:“孤抱你回椒房殿。以后几天的调教都在椒房殿和御花园。”他语气太过漫不经心,听起来好像楼信要受的淫刑并不重。
椒房殿装饰用度比之紫宸殿豪奢更甚,紫宸殿不仅是君王寝宫还是处理政事的场所,为提醒君王克己理政,不可沉迷声色享乐,内室连个镜子都没有,陈设简单。椒房殿里面就不同了,历来能住进去的基本是些高门贵女,有时她们还兼任大祭司,用度陈设富丽非常,里面还有处灵气充沛的活水温泉,虽然不比紫宸殿的大,但架不住温泉外修了处新宫室。
比起紫宸殿,椒房殿简直是处安乐窝,今日他还命人往里布置了刑房。
所以齐暄打算带楼信回去清理,椒房殿里玩起来也方便很多,毕竟皇后理应侍奉君主,里面一些助兴的小玩意儿他都可以用到楼信身上。
楼信闻言险些惊呼出声,齐暄抱着他回椒房殿?这不合规矩吧?再者说,他又不是普通的女子或双儿,被这么多花样玩下来,又没伤到走不动路。
他觑了一眼齐暄认真的脸色,温吞道:“陛下,臣可以自己走。”
齐暄现在哪容他拒绝,解释了句:“你今天承过雨露,走回去不妥当。”说罢当即穿过他膝弯,把人打横抱起,信信挑食惯了,果然如他想得一般轻。
楼信哪习惯被人这么抱着,突如其来的悬空感让他下意识勾住了齐暄脖颈,抬眸刚好对上齐暄清俊面庞,引得他心下意动,于是凑过去亲了下齐暄的下巴。
齐暄心想他的信信还真爱撩拨他,玩得厉害些信信又受不住,被楼信这一吻,他身下又起了欲望,但还是抱着人出了室内。
他们刚才胡闹的功夫,夜色已深,天空蒙上黑布,只余一痕新月与点点繁星,夜风微冷,吹乱了楼信发丝,他算是明白了齐暄为什么要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而非像今早在殿内那般给他披了层什么都遮不住的纱衣就拽着他去了浴池,原来是怕他着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