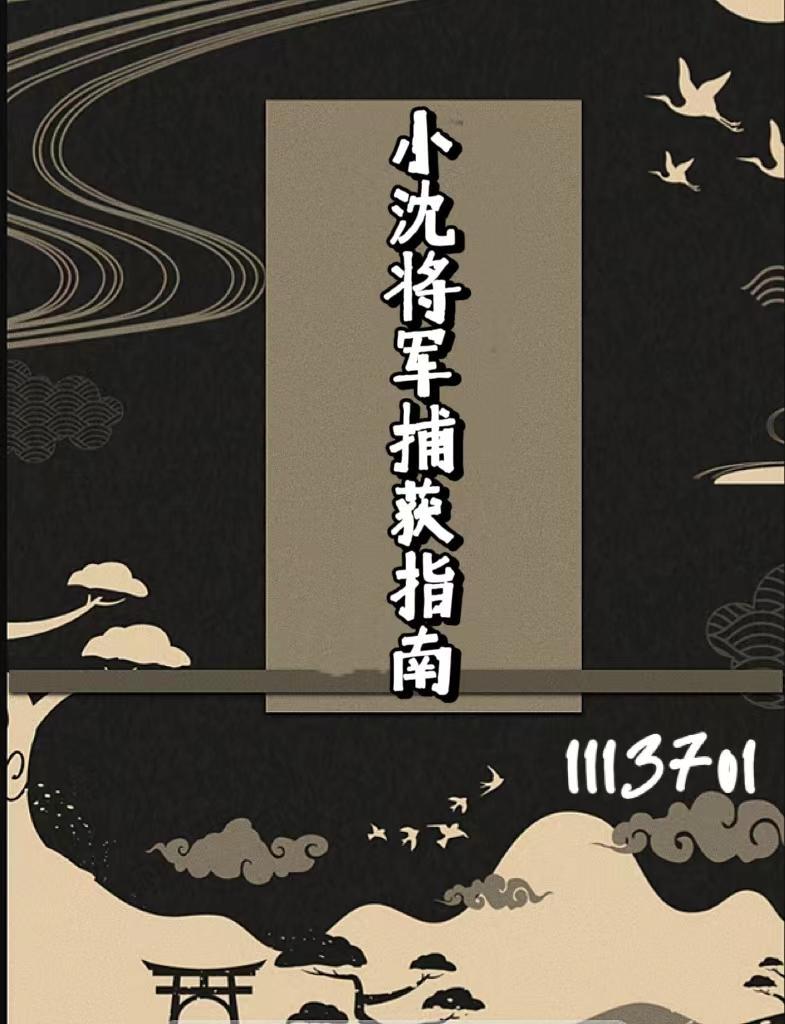笔趣小说>救赎穿书文推荐 > 第 66 章 沉默但也是默许(第1页)
第 66 章 沉默但也是默许(第1页)
房间里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清。
卡洛斯冲着来的方向拍打墙壁,那堵墙却闭得严丝合缝,半点也打不开。
原路返回的想法只能作罢,卡洛斯只能硬着头皮往深处走去。
越往里走,温度便越低,源源不断的冷气向他袭来,冻得他打了个冷颤。
房间里的温度至少在零度以下,与其说是密室,倒更像一个巨大的冷库。
经过刚才的争执,卡洛斯的浴袍已经完全没个正形了,他哆嗦着将袍子拢了拢,重新系好带子,才继续往前摸索去。
“嗒。”
“嗒。”
“嗒。”
随着卡洛斯的脚步,密室的灯一盏接一盏的打开。
开了灯,密室里的光线也并不算好,昏暗的白光甚至增添了一丝阴森冷寂的氛围。
位于房间中心的……是一个巨大的营养舱。
一具虫体正浸泡在半透明的营养液中,或许还混合着某种化学药剂,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奇怪的味道,颇有些刺鼻。
卡洛斯一步步上前,看清了眼前的一切。
一具枯树干一般的尸体,每片皮肤都皱巴巴的,就像是被剥了绑带的木乃伊,已经完全看不出虫形。
但那和他本人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小痣,还有干瘪的小尾钩,卡洛斯仅看了一眼,便呆在原地。
他怎么会不认识呢?
这……正是他的尸体。
卡洛斯有些呆愣地向前走去。
整个营养舱四周都环绕着蓝色的小花,珍贵的阿米朵花跟路边不要钱的野花一般,装满了整个房间。
梦幻而又美丽,就像是个最不愿醒来的梦。
他跨过脚边的花苞,扶开因他的动作而纷飞而起花瓣,一步步向前。
卡洛斯什么都想起来了。
那一晚根本不是梦。
雌虫跨进营养液,翅翼包裹着他,手拥抱抚摸着他,脸与唇亲吻着他,他们的身体紧紧相贴,以最畸形的姿态扭曲在一起。
灵魂深处传来的触感,皆为真实。
于他来说,那仅仅是一两天的时光,可是对于泽兰来说呢……
淡淡的营养液中浸泡着虫体,其表面正漂浮着一根羽毛。
他不会看错,那正是泽兰翅翼上的。
雪白羽毛湿漉漉的,被液体打湿了大半,分叉的绒毛已经被腐蚀的千疮百孔。
它似乎独自漂浮了太久太久,再也不能坚持下去。
要不了多久,便会彻底沉落。
陪伴着那具虫体,一起坠入舱底。
卡洛斯呆呆地环绕着四周,阿米朵花、他穿过的黑袍子,还有那盒他亲自送给泽兰的药膏,一切与他有关的东西,全都整齐地摆放在桌上。
而在桌子的正中央,悬浮着一颗晶体。
本该碎成粉末的晶体,近乎神迹一般粘合在了一起,虽然缺
了个小口子,但几乎完美无缺,只有凑近了才能看到上面怎么也无法复原的裂痕。
明明没有任何罩子,却也没有一丝灰尘,就像是抚摸过成百上千次一般。
卡洛斯站在原地,时间仿佛在这里停了下来,一阵阵眩晕涌上大脑,他感觉周围的一切都变得迟缓了起来。
从胸口泛出的疼痛,逐渐漫延向他身体的每一个部位,撕心裂肺的痛意已经淹没他的口鼻,连呼吸都开始变得刺痛起来。
做这些的时候,泽兰在想着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