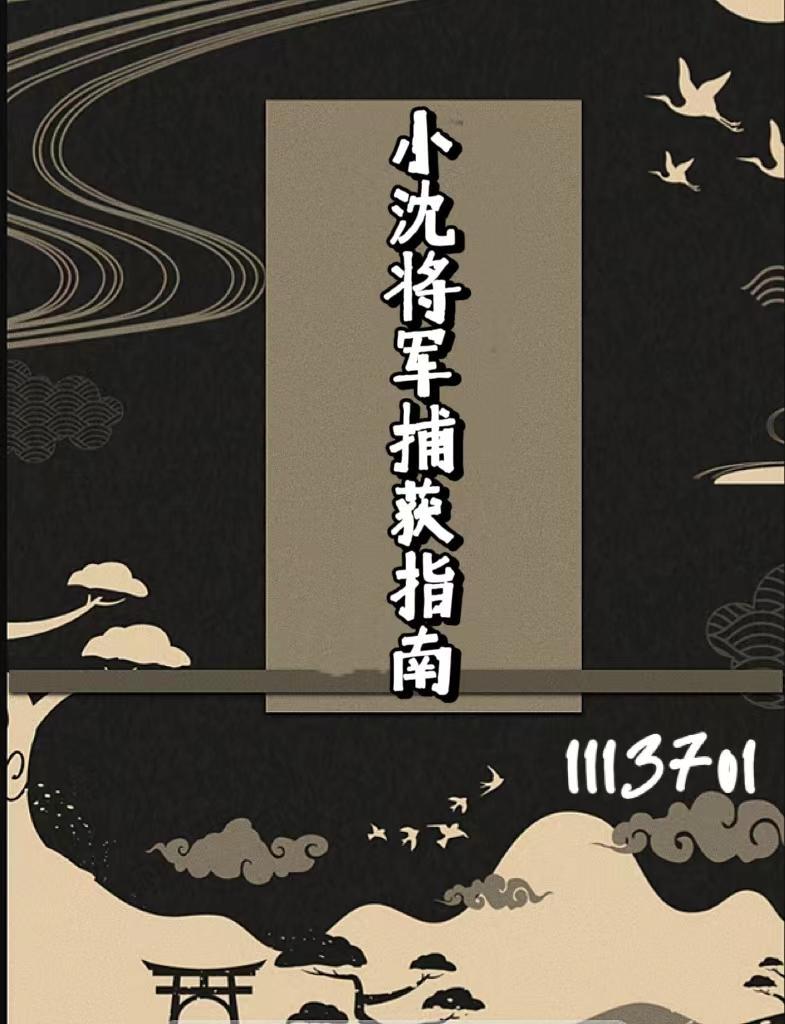笔趣小说>非典型攻略游戏 是个冬瓜 > 第61頁(第1页)
第61頁(第1页)
接著季隨安慰了幾句受到驚嚇的學生,將他們打發去上課,自己等來了姍姍來遲的王老師。
花盆是從天台掉落的,這些花盆本來是學生們參加種植活動的成果,由於花都敗了,就全部搬上天台當成雜物放著。
花盆很重,且今日無風,但王老師堅稱這只是意外,找了清潔工來打掃。
季隨脫身後,也前往了天台,在王老師口中鎖著的天台門現在卻大敞開著,梁久蹲在天台邊緣正查看那些花盆,聞聲轉過頭:「應該就是這裡的花盆。」
「王老師也這麼說。」季隨道,「有看到什麼人嗎?」
「沒有。」梁久奇怪道,「怎麼這麼問?」
「食堂和宿舍的事故,都有明確的嫌疑人,所以我想確認一下。」
「嗯,確實……」梁久摸著下巴沉思了一下,「但是圖書館的事就沒法鎖定人,所以說Boss也不一定會露面。」
季隨想起一晃而過的那個人影,那大概就是Boss之一,只是他不好跟梁久解釋自己是怎麼看到的。
「對了,你是怎麼知道花盆掉了的?」梁久問。
「它倒下來的那一刻擦在了牆側,聲音很明顯。」季隨回答道。這是實話,他確實是在花盆還沒墜到三樓前就聽到了聲音,否則等看見花盆再行動的話就來不及反應了。
梁久無不敬佩地感慨:「我壓根沒注意別的聲音。」
「很正常,我只是習慣了用聲音當眼睛。」說話間,季隨已經走到了天台邊緣。
梁久連忙叫住他:「停,別往前了。」
季隨的鞋尖碰到了天台邊緣的小坎,這個坎僅僅有他半個小腿高,稍稍抬腿就能邁過去。
他閉著眼睛,感受著這裡不疾不徐的微風,忽然,身後傳來什麼東西炸裂的聲響。
眼前驟暗,那炸裂的聲響就響在離他鞋邊不到一尺的地方,季隨下意識地避了避,又踩到了什麼,隨即又是「啪」的一聲。
是摔炮。
這些裹成小球的摔炮是兒時常見的一種,一般不會傷人,只是響聲會嚇人一跳,當然,如果近距離用力投擲的話,那個力道也有可能使炮在人的身上炸開。
一種會被傷到的恐懼湧上心頭,他不由自主地躲開了那些極近的聲響,往自己也不知道的方向後退。
這些炮到底是哪來的?
啊,對了,這是老師們的懲罰工具,他們說我暴躁、愛發脾氣、不服管教,也從不認真上課,所以他們忍耐不下去了,要懲罰我,要讓我知道害怕,他們管這個叫作「對症下藥」「因材施教」。
他們一邊發怒,一邊朝我投來這些小小的炮仗,然後被我四處躲避的滑稽樣子逗得哈哈大笑。
到處都是炮仗,到處都是嚇人的聲音。
好想逃,好想逃。
「喂!!!」一聲大吼振聾發聵。
季隨猛然回過神,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半懸空的姿勢,梁久揪著他的衣領用力往回拽,才把他拽了回來。
「季隨?季隨?醒醒!」似乎是擔心他再往前走,梁久直接把他摜倒在地,開始拍他的臉。
突然遭受無妄之災的季隨默默撥開他的手:「醒著呢。」
梁久:「我剛才叫你,你沒反應。」
「剛才出現了幻覺。」季隨緩緩坐起來,一隻手搭在屈起來的膝蓋上,「我可能知道這位Boss生前經歷過什麼了。」
「Boss?」梁久納悶,「怎麼又是你中招,我就沒事?跟昨天圖書館那個一樣?」
「昨天的原因不明,至於今天這個,」季隨摸了摸自己的眼睛,「可能因為我們都是盲人吧。」
他掃了一眼系統頁面:「我沒有觸發什麼仇恨標記。」
危險期里即使沒有仇恨標記,惹惱了Boss也會遭到攻擊。
但季隨並不覺得自己得罪了那位盲人同學,總不能是因為沒讓他成功砸死人,所以惱羞成怒了吧。
不,在這個副本里,學生與老師的對立性更強,從盲人同學的經歷來看,應該也是敵視老師而非同學,季隨剛才是保護學生的那一方,這個舉動應該不會激怒盲人。
若說單純敵視他「老師」的身份,那梁久應該比自己更容易中招才對,而且只要梁久清醒著,自己也不可能掉下去……
難道盲人同學只是單純想告訴他真相嗎?
季隨壓下不解,視線掃過天台的角落,隨後明知故問道:「天台上有別的空間嗎?」
「有個小房子。」梁久瞥了一眼後道,「上著鎖,不過我應該可以弄下來。」
跟南軒那奇妙的開--鎖技巧不同,梁久完全是用暴力開鎖的。
一開門,撲面而來的灰塵就把季隨嗆了一下,屋子裡像是一個倉庫,放著一些閒置的舊書架以及壞掉的桌椅,不大的空間被堆得滿滿當當。
季隨用盲杖撥了撥地上的東西,發現了一掛鞭炮,雖然不是摔炮,但也很可能是會激怒Boss的東西,季隨沒有去碰。
梁久從書架上隨便撿起了一個文件夾,走到門口借光,片刻後驚訝地出聲:「是以前的事故記錄。」
季隨偏了偏頭,倚在門側,等著下文。
「這本是上個學期的記錄……這數量,每天都得發生一兩次事故吧,如果沒有被消除記憶,估計全校師生早就該辭職的辭職,該退學的退學了。」梁久快地翻完一遍,才仔細看了下內容,過了一會兒,他合上書,眸色沉了沉,「沒有學生死亡,雖然每天都有人受傷,但是沒有死亡,相比之下,死亡的老師足夠把全校的老師都換一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