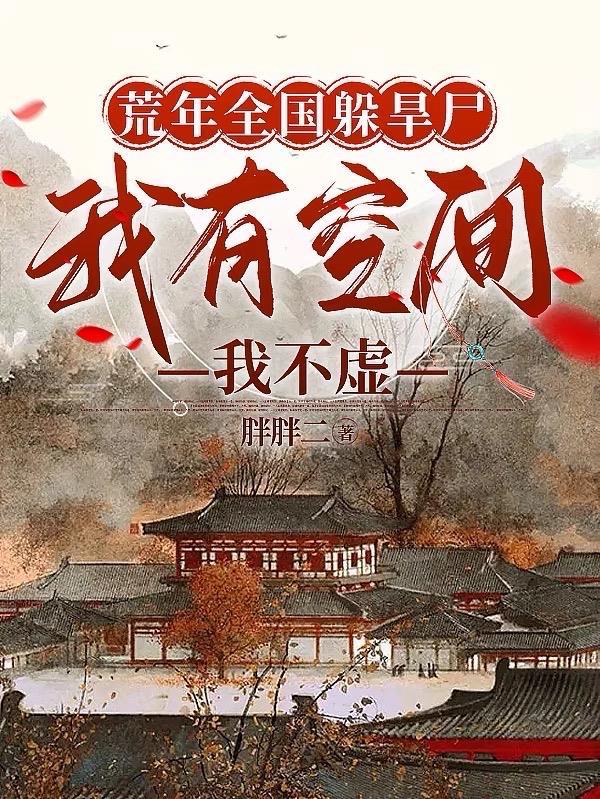笔趣小说>眉黛落的男主是谁 > 第32章(第1页)
第32章(第1页)
任峰即便武艺不精,却也学了几手,迅速抓住了她的手臂,低笑道:“苏姑娘急着去哪里?左右无事,不若跟本公子去满福楼坐坐?”
苏眉儿挣脱不得,感觉到他的手慢慢收紧,指尖轻佻地摩挲着自己露在宽袖外的手腕,霎时浑身起了一片的鸡皮疙瘩。
这人的目的显然而见,在任府门外,竟然丝毫没有避嫌的意思,颇为肆无忌惮。
硬拼硬并非良策,苏眉儿的嘴角勉强扯了一分浅笑,垂眸道:“任大公子这眉心暗沉,全身气息虚弱,恐怕近日有祸事降临。”
她说得认真,一双漆黑晶亮的眼眸直直地盯着自己,让任峰心下一跳,只觉头皮发麻,仍是嘴硬道:“鬼神之说,如何能信?想不到苏姑娘也继承了苏先知的衣钵,总算是后继有人了。”
他这厢想扯开话题,苏眉儿却是靠了过来,纤细的手臂搭上了任峰的肩头。
“任大公子,可是觉得最近脚下虚浮,双肩似是压着重物,夜里又睡得不安稳?”
任峰一愣,确实如苏眉儿所说,自己这些时日以来总觉得疲惫,浑身没有力气,还精神精神不济。瞅着她,有了些动摇。
“苏姑娘如此笃定,可是有破解之法?”
小心陪着笑,任峰松开她的手臂,脸上多了一丝讨好。
苏眉儿捏着指头,蹙起眉。片刻后,见任峰急得一头汗,这才慢悠悠地道:“依奴家之见,两月内,任大公子最好不要离开院门一步为好。”
“两个月?”任峰大吃一惊,让日夜出府吃喝耍玩的他乖乖呆在自己的院子里,简直是一种折磨!
“苏姑娘,就没有别的法子?”
苏眉儿抬了抬眼皮,不悦道:“既然任大公子不信奴家,奴家亦无话可说。”
说罢,她冷哼一声,转过身便进了任府,留下任峰苦着脸,神情纠结不已。
回头瞧了一眼,苏眉儿唇角一翘。想到几句话便忽悠住这人,实在是心花怒放。
任峰夜夜笙歌,在勾栏院胡混,这身子自然是虚得紧。即便有些功夫底子,也经不住这样的耗损,当然会脚步虚浮,浑身无力了……
可是这好心情没有持续多久,新管家毕恭毕敬地站在她的身前:“苏姑娘,老爷有请。”
不知任恒为何来寻她,苏眉儿却拒绝不得。
仍旧是上回的主屋,房内却只得任家家主,不见六夫人如倩。
她规规矩矩地行了礼,在任恒的颔首下缓缓落座。
新管家奉上热茶,便恭谨地退出了院外,由始至终没有抬头,一举一动小心翼翼。想必上一任总管的惨况,震慑了不少人。
“这是新到的春茶,苏姑娘不妨尝一尝。”任恒神色是少见的温和,却让苏眉儿越发忐忑不安。
“不知家主请奴家过来,所为何事?”实在受不住这些人转弯抹角的话,她索性单刀直入地问起。
“看苏姑娘也是个爽快人,我便不兜圈子了。”任恒低头抿了口热茶,指尖在杯沿轻轻一抚,漫不经心道:“不知苏姑娘与峰儿相处得如何?”
苏眉儿一怔,不知道他为何突然提起任峰,斟酌地答道:“大公子一表人才,又是任家嫡子,自是人中龙凤。”
恭维的话听得多了,却依旧没有影响任恒的好心情:“峰儿的性情如何,我这个当爹的看得清楚,苏姑娘不免谬赞了。”话锋一转,这位任家家主忽然道:“我能瞧出峰儿对苏姑娘的另眼相看,不知姑娘意下如何?”
闻言,苏眉儿端着杯子的手一抖,险些将热茶泼了。
若是当面数落任峰的不是,不免拂了任恒的面子。可是如果没有拒绝,听家主的意思,还想做一回月老?“奴家出身卑贱,万万不敢高攀任家大少的。”
思索半晌,苏眉儿终归是寻到了一个妥当的理由。
只是任恒显然不吃她这一套,点头道:“苏姑娘能力卓绝,倒是峰儿高攀才是……不知苏姑娘家中都有些什么人?”
她双唇一颤,结结巴巴道:“父母亡故,早已不在人世。可是奴家大小颠沛流离,不像平日的大家闺秀,经常抛头露面,再就是……”
苏眉儿咬着唇,豁出去了:“奴家并非清白之身,怎能误了任大公子?”
任恒听罢,不过睨了她一眼,慢条斯理地道:“任家的人走南往北,什么世面没见过,抛头露面又算得了什么。”
“有些事该说,有些事却不该说,如夫人可是明明白白地看见了苏姑娘手臂上的守宫砂,姑娘又怎能胡言乱语,自毁名声?”
那天如倩突然拜访,原来为的是看清她的守宫砂。
苏眉儿一时语塞,在这个老狐狸前,根本无计可施。
她不愿就此受人摆布,一辈子被困在任府之中,不管不顾冲口而出:“任老爷,奴家已经答应阁主,明日便随他回祈天阁。”
“炎阁主?”任恒双眼一眯,眸底一道凌厉的精光转眼即逝:“苏姑娘可知,祈天阁是什么地方?跟着阁主回去,又代表了什么?”
苏眉儿见他似是动摇,连连点头:“奴家当然是晓得的……”
看着她似懂非懂的模样,任恒嘴角的笑意不由多了几分讥嘲,仿佛在嘲笑苏眉儿的无知:“祈天阁只认钱不认人,买命的事做得不少,结了许多仇家。据说阁主好男色,阁中清一色都是相貌秀美的少年,且武艺卓越,皆是一等一的好手。”
“苏姑娘此番去祈天阁,撇开其中身份尴尬不说,还得日夜担心有性命之忧。我与姑娘相识一场,实在不愿眼睁睁看着你往火坑里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