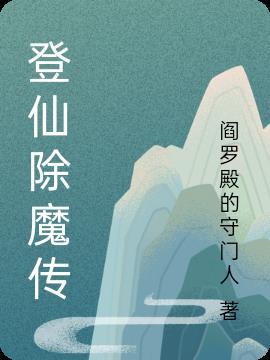笔趣小说>死光a重型激光武器真的假的 > 第20章魔力的源泉(第5页)
第20章魔力的源泉(第5页)
“算了吧,干草堆,”理奇低声埋怨着“太久了。”
“带、带、带我们到那、那儿去,班恩。”比尔站在他的身后,又说了一遍。
他们跟着班恩,离开那块已经不存在的空地,向肯塔斯基河走去。流水声越来越响。
但是还是当他们差点掉进河水里的时候,才看到那条河:河堤边缘已被各种植物纠结缠绕。班恩脚下的河堤崩溃了,比尔一把拽住他的脖颈,把他拉了回来。
“谢谢。”班恩说。
“不用谢。从、从前,你拉、拉我上来。走、走这条路、路吗?”
班恩点点头,带着他们沿着杂草密布的堤岸,穿过茂密的树丛往前走。心里想当你只有4英尺5英寸高的时候,一弯腰,就从茂密的树丛下钻过去了。哦,一切都变了。今天我们得到的教训就是变化越大,就会有更多的事情发生变化。
他的脚绊在什么东西上,砰地摔倒在地上,头差点磕在泵站的水泥圆柱上。那根柱子几乎完全埋没在一簇黑麦丛里。他站起来后,才发现脸、胳膊、手都被黑莓刺刮破了。鲜血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他俯身看看是什么把他绊倒了,可能是树根吧。
但是那不是树根。而是检修孔上的铁盖,有人把它掀了下来。
当然,班恩想。我们干的,27年前。
但是还没有看到铁锈上新留下的刮痕,他就知道那根本是不可能的。那天水泵坏了。迟早会有人来修理,会把盖子重新盖好的。
他站起来,5个人围着圆柱,往里看。他们能听到微弱的水滴声。除此一片寂静。理奇把艾迪房间里的火柴都带来了。他点燃了整整一盒,扔了进去。他们看到圆柱潮湿的内壁和寂静无声的抽水机。再也没有什么了。
“可能会要好一阵了,”理奇不安地说“不一定恰巧——”
“肯定是最近的事,”班恩说“自上一场雨后。”他从理奇手里拿过一盒火柴,擦亮一根,指着铁盖上新的擦痕。
“下、下面压着什、什、什么东西。”就在班恩摇灭火柴的时候,比尔说。
“是什么?”班思问。
“看、看、看不清、清、清楚。好像是一根皮、皮、皮带。你和理奇帮我把它翻、翻、翻过来。”
他们抓住铁盖,像翻一枚巨大的硬币那样把它翻了过来。贝弗莉擦亮火柴,班恩小心地捡起铁盖下的那个皮包。他拎着带子。贝弗莉正要摇灭火柴时,突然看到比尔的脸c火柴烧到了她的指尖,她才清醒过来,赶忙扔掉火柴。“比尔,是什么?出什么事了?”
比尔的眼睛久久不能离开那个挂着长长的背带、已经蹭破了的皮包。他突然想起了他为她买这个皮包的时候,那家皮具店的收音机里正在播放的那首歌的名字——夏夜。顿时觉得口干舌燥。
这又是一个小把戏、幻觉。她在英格兰。这只是一个鬼花招,因为它害怕了,对,当它叫我们回来的时候,它也许不像从前那么自信,肯定是,比尔,理智点儿——世界上有多少长背带、刮破了的皮包呢?一百万个?一千万个?
也许更多。但是这样的只有一个。他在布尔班克皮具店为她买了这个包,当时后面屋子里的收音机正在播放着夏夜这首歌。
“比尔?”贝弗莉摇晃着他的肩膀。
“比尔,出什么事了?”理奇低声问道。
比尔尖叫一声,从贝弗莉手里抓过火柴,擦亮一根,猛地从班恩手里拉过那个皮包。
“比尔,上帝,怎么——”
他拉开皮包,把所有的东西都倒出来。掉出来的都是奥德拉的东西。那一刻他简直失去了控制。在面巾纸、口香糖、化妆品中,有一盒奥德拉最喜欢的薄荷糖还有她签约阁楼的时候,弗雷迪送给她的镶嵌着珠宝的粉盒。
“我妻、妻、妻子在下面。”他说着,跪在地上把所有的东西都塞进包里。他无意识地捋了捋早已不在的头发。
“你的妻子?奥德拉?”贝弗莉瞪大了眼睛,惊讶极了。
“她的皮、皮、皮包。她的东、东西。”
“上帝啊,比尔,”理奇低声说“那不可能,你知道——”
他拿出她的鳄鱼皮钱夹。打开来,伸到理奇面前。理奇有点着一根火柴,看到一张他在好几部电影里都见过的脸庞。奥德拉的加州驾照上贴的那张照片不像电影里那么漂亮,但是毫无疑问是她了。
“但是亭、亨、亨利死了,维克多、贝尔茨也死了,谁抓住了她?”他站起来,目光灼热地看着大家。“谁抓走了她?”
班恩拍着比尔的肩膀。“我想我们最好下去查个水落石出,嗯?”
比尔看着大家,好像不知道班思是谁,然后他的眼睛明亮起来。“对、对,”他说“艾、艾、艾迪?”
“比尔,我真的为你感到难过。”
“你能爬爬上来吗?”
“从前爬上去过。”
比尔弯下腰,艾迪用右臂钩住比尔的脖子。班恩和理奇用力推着他,直到他的双腿能钩住比尔的腰。比尔慢慢地抬起一条腿,迈进圆柱口的时候,班恩看到艾迪紧闭双目那一刻,他觉得自己听到从树丛那边传来世界上最难听的冲锋号角。他转过身,想着会看见亨利他们3个穿过浓雾、穿过树丛追踪而来。但是他只能听到微风吹动竹林树叶沙沙的响声。如今他们的死敌已经都死了。
比尔抓住粗糙的水泥圆柱口,一步一步摸索着往下走。艾迪把地搂得死死的,他几乎喘不过气来。她的皮包,上帝啊,她的皮包怎么会到了这里?没关系的。但是如果你就在这里,上帝啊,如果你正在听着我的祈祷,就求你保护她平安无事吧,不要因为我和贝弗莉今晚所做的一切,因为那个夏天我所做的一切而让她受苦
是那个小丑吗?如果是,我不知道是否上帝能救了她。
“我很害怕,比尔。”艾迪低声说。
比尔的鞋已经触到冰凉的水洼。他爬下去,想起了这种感觉,阴冷潮湿的味道,想起了这个地方带给他的压迫感还有,他们遇到了什么事情?他们怎么走过这些下水道?他们到底去了哪里?
又是怎么走出去的?他还是一点也想不起来;他想得起来的只有奥德拉。
“我也、也怕。”他半蹲着,冰凉的水灌进他的球鞋和裤管,他不由得皱了皱眉头。他把艾迪放下。他们站在深及小腿的水洼里,看着其他的人一个一个爬下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