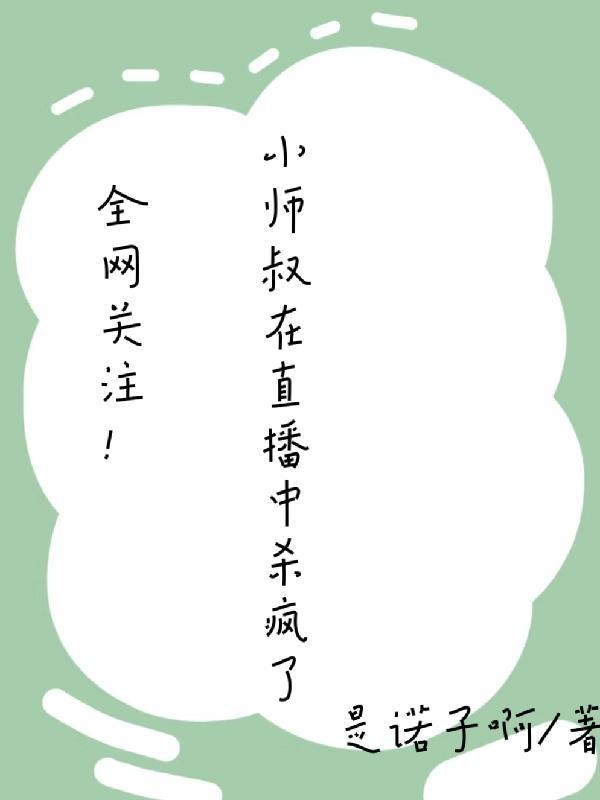笔趣小说>温带植物by雪碧oo是双洁吗 > 第31頁(第1页)
第31頁(第1页)
溫遇旬攔了一下:「還喝?」
沈榆沒什麼太多感覺,只覺得有點飄忽,興奮更多點,還記得解釋:「我聽很多公司里的前輩說他們寫詞的時候喜歡小酌,說那樣很有感覺,我想試一試。」
開的也是白酒,年份不如王禛星的那瓶久遠,酒液呈現毫無攻擊性的透明。
如果沈榆堅持伸手的緣由是明知故醉,想從酒精作用中獲得一點快樂和靈感,那麼溫遇旬移開手,故意放任沈榆追尋不好把握的微醺境界,原因似乎不好考究。
畢竟連溫遇旬自己都不明白原因,好像陰謀的助推手,就這樣看沈榆沒有節制地一杯接著一杯。
沈榆沒喝醉過,他覺得臉燙,頭昏,但知道不能在人多的地方耍酒瘋。
他自己沒意識到,坐他旁邊的兩個人都有體會,沈榆話變得很多,但輕易不敢找溫遇旬說,和溫玉菡聊得很多。
岑漫搖看到兩個年紀最小的聊得投機,還有些意外,說:「小榆下次回家吃飯帶著小菡吧。」
在她印象里,沈榆就沒有和哪個女孩子玩得多好,走得多近。
快散場的時候溫玉菡旁敲側擊地想加沈榆的聯繫方式,加完了不滿足:「哥,能不能看在我是長眠灣粉絲的份上給我簽個名?」
沈榆反應變得很慢,和溫遇旬一起坐上了車后座,搖下車窗說:「簽名沒有,但是可以給你我以前考試的卷子。」
溫遇旬看他的眼神變得深,但安靜,提醒沈榆把探出車窗外的手臂收回來:「走了。」
回程的車裡和來時一樣靜,溫家聘任的司機向來沉默,溫遇旬以為沈榆喝多睡著了,轉頭一看,那人分明睜著眼,盯著正前方的駕駛位後背看。
臉全紅了,剛剛和溫玉菡說話的嘰歪勁兒,到溫遇旬這裡好像又不頂用了。
車子一路駛向北城區,時間不上不下,不到晚高峰,因此很快到達停車場。
司機停好車,對溫遇旬說:「小溫先生,我先走了。」
溫遇旬點點頭,從他手裡接過車鑰匙,司機就先下了車。
如果沈榆不下車的緣由是酒精上頭,反應遲緩,睜著眼睛也仿若入定活佛,那麼溫遇旬現下陪他一同坐在地下車庫裡這昏暗的一處,原因似乎也同樣不好考究。
起初,兩個人都沒有什麼動作,過了一會兒,溫遇旬聽見離自己不到一臂距離的沈榆的入定處傳來一陣細碎的動靜。
沈榆用沾血的手掌握住溫遇旬的手腕,嘴裡不清不楚:「終於沒人了。」
溫遇旬對喝醉的沈榆就不像平時那麼刻薄,這也正是他想要的,就由著沈榆碰他。
沈榆拉著溫遇旬的手貼上自己的臉:「你手好涼。」
「沒有,」溫遇旬雖然沒拒絕,但也沒有別的動作了,「是你喝多了,臉太熱。」
「嗯?」沈榆閉著眼睛,但知道嘴硬,「我沒有喝多,你不要亂說。」
溫遇旬的手掌緊密地貼在沈榆的臉頰上,接著又被帶到額頭,眼皮上,好像掌紋里的每一處都塞下沈榆的皮膚和身體,看起來那麼親密,但是兩個人又坐得很遠。
「沈榆,」溫遇旬聲音有點沉,「我是誰?」
沈榆看他一眼,然後用不清澈的眼神給出清醒的答案:「溫遇旬,我怎麼可能會忘記你。」
「你不會嗎?」手掌碰到沈榆細密又長的睫毛,十指連心不是亂說,溫遇旬心都癢。
然而他做的反問好像讓沈榆生氣了,他眼睛睜開瞪人:「不會。」
「你會。」
溫遇旬出聲譏諷道:「我是不知道你想要做什麼,分手的時候斬釘截鐵,沒有一絲轉圜的餘地,明明給我的理由是害怕我的聲譽受到影響,現在為什麼又巴巴地貼過來,在房間門口把我拉住,求我睡你?」
他仿若委屈了,要把所有的苦水倒乾淨,手掌不再任人擺布,脅住沈榆的下巴掰過來,強迫與自己對視。
他語氣還算平靜,只是手上力度不小。
「剛才和溫玉菡聊得也很投機,嫌我離你太近,還要連人帶椅子往她那裡挪過去。」
溫遇旬知道自己言論無稽,但好像是故意要惡意揣測,理性是對外的,對沈榆一直衝動:「需不需要我為你牽線?還是說對我和顏悅色是為了勾搭她?」
沈榆心驚膽顫:「我沒有!」
溫遇旬手上一串檀木珠子散發出好聞的香氣,大約是帶著禪意的靜心功效,現下就卡在沈榆鼻下,卻完全沒有作用。
「你別忘了,要跟我是亂搞,那跟她也是一樣。」溫遇旬不理會沈榆捱不住下顎疼痛,在他身上沒多少威力的捶打。
他也覺得自己面目可憎,想聽一個沈榆為何反常的回答,拷問之前還要灌醉犯人,想著或許借酒精能讓沈榆大膽一點。
沈榆不說,可他又實在想知道。
溫遇旬骨子裡就是驕傲的,家庭和能力帶給他無窮大的底氣,他這一生波折確實不多,沈榆算是其中少見的一浪。
他與自己較勁,較到現在,也早就分不清是心不甘還是放不下了。
犯人受不住拷問,急忙投誠:「我對溫玉菡沒有想法,我只有你……」
沈榆說到一半突然停下來了,看著溫遇旬,眼睛眨一下,眼底湧起來一點水光。
「你不知道,你都不知道,我差點就失去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