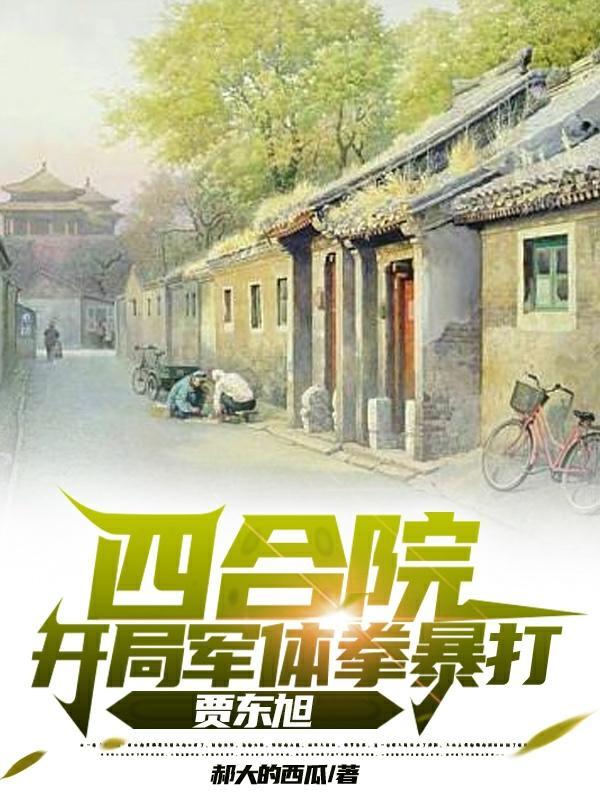笔趣小说>追昔txt > 第74页(第2页)
第74页(第2页)
被子够大,将两个家夥都罩住,顾灵运很晕,很热,他把腿格外地大张,方便男人的动作,在对方舔弄的同时,他也疯狂地回应。
纠缠,厮缠。
六年。
其实不一直在想著这个家夥吗?下意识里一直等著这天……
被刺入时的痛似乎可以忽略不计,只感觉到彼此融为一体的巨大的幸福感。
仿佛一颗心都落到实处。
同志,谁管呢,管他娘的是不是gay,他想这麽过,想跟这个家夥这麽来,狠狠地干,他想。
火,从内到外都燃遍了。
背後,比所有梦境更激烈更疯狂,男人狠狠地侵犯。
那家夥知道所有他的敏感点,挑弄他几乎已经是本能,他随意地换著角度顶入,他就喘得吸不了气。
一次次被深深地插进,眼前阵阵发黑,混合著极度的亢奋和几欲昏迷的生理恐惧,他死命地掐住男人的胳膊,觉得已经到了极致却还能更强,以为下一刻会失去知觉,却会迎来更汹涌的活煞煞从尾椎直冲向後脑的电击般的快感。
无法用任何言语形容。
发烧,他没劲儿,被插得东倒西歪,像是浪尖上的小帆船。
哑著嗓子,他开始嘶叫,可那叫声听著更像呜咽或是诱惑的低吟。
安湛疯了。
他发了一轮,就将人弄到浴室,放慢整池热水,整个抱进去将那里洗干净,洗著,却又开始第二轮。
“你真他妈是牲畜啊,我烧著呢!”
青年病恹恹,脸颊红漾漾的,双眼半眯著,快乐兴奋还没从神经内退去,嘴唇湿润得像是染上了珠光,在男人眼里是惊人的独一无二的美。
混蛋就混蛋吧,禽兽就禽兽吧。
男人已经发过一回,这会儿有了底气,惦记起他老到的经验技术来。
轻轻吻著他的唇:“烧著,里面不是热嘛……”
靠!
顾灵运恼了,拿他自己的话堵他呢!
不过实在没力气再争辩,身体已经不由他自己控制。
不过实在没力气再争辩,身体已经不由他自己控制。
病著的时候总是孱弱,不止身体,更有内心。会有特别的不安全感。顾灵运对疾病更有深一层的恐惧。陪伴癌症晚期的母亲,那几个月让他对健康极为看重,因为死亡本身不可怕,但是时刻濒临死亡的绝境实在煎熬。
也许,他想,就算最爱的人在身边,也不能减轻死亡的阴影和恐惧。
如果安湛知道这个时候怀中的人想著的竟是这些,不知作何感想。
当然他不知道,他正全神贯注地仔细悠游地品尝大餐。
水微烫,顾灵运微闭著眼睛,他还是不舒服,关节有些酸软,没力气,但是触感却比平时更敏锐。
他能清晰感受到男人的每个吻,从大腿内侧上移,慢慢地,似乎蜻蜓点水,又似乎挑逗撩拨,他始终忍著,只是在水下的手紧紧握住男人的胳膊。
啊──
被含住。
靠,这是水里,能含上多久?也不嫌脏!
不过,那舌头真是灵巧如蛇,算是搏命出演了吧?比他想象中的时间要长很多,肺活量可真够大,折腾这麽久,还玩花样。
顾灵运半眯著眼睛看著水里的大头颅,身体兴奋,心却很柔软。
“以前……没这麽弄过。”他轻轻感叹。
男人猛地从水里冒出来,大口大口呼吸空气:“舒服麽,还硬不起来哦,年纪轻轻的……”口气有点坏坏。
“我发烧呢!”刚才又不是没硬!
安湛笑得邪性,整个将他抱起,用干毛巾草草地擦了下,又回到床上。
两个人叠在一起,顾灵运的全身都被舔过,吻过,直到那里被慢慢含住,过程漫长又精细,快感和焦躁并存,他呼吸急促,脖子後伸,本就晕著的头脑根本再不能思考,只剩下最本源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