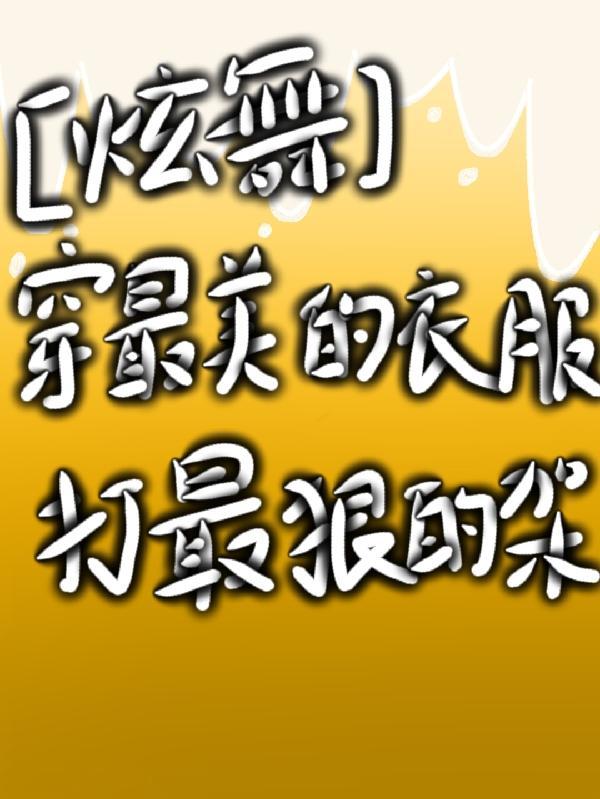笔趣小说>漂亮的小哑巴季洛免费阅读 > 第20章 放了我吧求求你(第2页)
第20章 放了我吧求求你(第2页)
“呦?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傅子修嬉笑道,“不是跟你那小哑巴郎情妾意呢吗?聂总竟然有空翻我的牌子?”傅子修不死不休。
“不来算了。”聂北弦说着,就要挂断电话。
“诶诶诶!别挂别挂!陛下赏脸,臣妾喜极而泣,感激涕零,这就滚过去。”
紫禁阁是一家以皇宫元素为特色的会员制高级会所。
聂北弦和傅子修前后脚到,相隔不差五分钟。
傅子修以他一贯的慵懒姿态倚靠在椅子上,白皙的手臂随意地搭在椅背上,桃花眼微微上挑,带着一丝不经意的探究,他轻声问道:“心情不好?”
语气带着轻松,却难掩其中的关切。
聂北弦脸色依然蒙着一层阴郁,也隐着几分忧伤,沉默着拿起酒杯跟傅子修碰了碰,然后一饮而尽。
捏着酒杯的手指骨节分明,带着修长而又遒劲的美感,却也泛着冷白的微光。
傅子修见状,不禁试探性地问:“为了小哑巴?”
聂北弦又是沉默。
傅子修眨了眨漂亮的桃花眼,有些意外。
跟聂北弦厮混了小三十年了,他对这个小的了解程度可以说已经细致入微到每根头丝的纹路。
在世人眼中,聂北弦冷血残暴,六亲不认。
四年前,不但凭借打垮林氏集团而成功掌控了海晟集团的经营管理权,拿下仅次于他那个董事长爹的3o%的集团股权,还一举收拾了谋害他亲妈流产而亡的小三上位的继母,杀得那几个同父异母的弟弟片甲不留。
没人知道,这万年冰块的心里,也有着不为人知的柔软。
只是,傅子修万万没有想到,半个月前还口口声声要小哑巴生不如死的人,现在反倒为了小哑巴的一举一动来找他来喝闷酒。
“你不会真的喜欢上小哑巴了吧?”他试探而又诧异地问道。
聂北弦垂着眸子,低沉地说,“什么是喜欢?”
傅子修吊儿郎当地调侃道:“聂总,您大晚上的翻我牌子,就是为了跟我讨论这种小学生问题?”
聂北弦冷冷嗤笑一声,自顾自满了一杯酒,再度一饮而尽。
眸色渐渐染上微醺,“带着目的接近你,千方百计达到目的,之后就毫不犹豫地离开你,整整四年……一次也没来找过你。”
聂北弦说着,顿了几秒钟,眼中的伤微颤着冷幽的光,“呵……现在,你把他从那个狼窝里救出来,他却还是挣了命地想要离开。”
他闭了闭眼,睁开的时候,眼尾染上薄红,“他到底有多喜欢你?”
他的反问,有些微微颤。
傅子修抿了抿唇,眸色染上几分同情和共鸣的理解。
他跟聂北弦貌似南辕北辙,实质上却太像了,他是万花丛中滚过,丹心不知付谁;而聂北弦,则是从不付出感情的万年冰块,一旦用了心,就全都化成柔情春水,一不可收拾。
都他妈为情所困,贱得慌!
“伤心了?”他低低地问,难得正经,觉得自己的心也有点跟着疼。
“呵……”聂北弦嗤笑,“不过是个小哑巴。”
聂北弦冷冷地说着,眼中的伤却比那瓶中红酒还要浓。
“可唯独这小哑巴,叫我们的铁面阎王放不下!”
“铁树开花了!你呀,是对小哑巴动了真情了!”他说着,给俩人倒满了酒,与聂北弦一起干掉。
聂北弦放下酒杯,“他值得吗?”眼神迷离,口中悲催。
傅子修斜睨了他一眼,“那林琅呢?林琅值得吗?我听说她也从米国回来了,你们俩前后脚去了米国,一呆就是四年,就没生点儿啥?”
他凑近聂北弦,探究地问:“你那闺女,不会是林琅生的吧?”
聂北弦猛地推了他一把,“滚蛋!少跟这儿脑嗨!别人不知道,你还不了解,怎么可能?”
他怎么可能跟一个女人上床?
他说着,又想起什么,继续道:“你也给我离那个疯女人远点儿,她要是找你,无论她冲你还是冲我,你都不许理她。”
傅子修懒散地打了个酒嗝,“是是是!陛下,臣妾遵旨。”
“滚蛋!”聂北弦轻笑,“我后宫里可装不下你这个海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