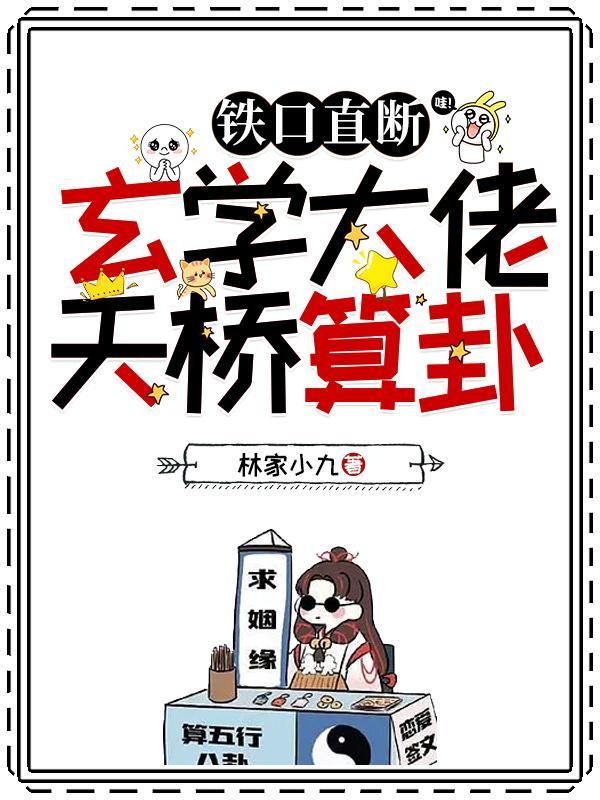笔趣小说>弹不了九度怎么办 > 第166章(第1页)
第166章(第1页)
“我就是你的右手。”
乔横林说,然后有模有样地展示给季鹤看,其实弹得很糟糕,听到耳朵里有些折磨,但季鹤仍然把左手搭了上去,跟他合奏了一曲。
乔横林十分介怀的事情,季鹤却不太在意,那个时候,他已经学会了左手习字,这对他来说并不难,相反重新握笔、练习笔画的行为让他有种很奇妙的感觉。
尽管刚开始不太工整,但季鹤从不气馁,他认真地修正每一个大字,就像修正以后的人生一样,一撇一捺,一点一横,过程跟结局一样幸福。
新年的时候,乔横林窝在床上看小说,烟花和鞭炮在门外炸呀炸,他都没有动弹。
季鹤洗完澡到卧室,乔横林就爬起来给他吹头发,便宜的老式吹风机早就被他丢掉了,现在是用兼职第一个月工资买来的名牌吹风机,有三档调温,先用高档,再用中档,最后用低档,乔横林一个步骤都不会错过,仔仔细细、认认真真地对待每一根头发。
季鹤问他在看什么小说,乔横林趴在他的脖子上,轻轻咬了季鹤的锁骨。
他终于知道为什么季鹤之前说他推荐的小说,自己一定没有看过,因为这本书的写了这样一句话:
「在这个世界上,你是我找到的唯一的亲人。」
如果乔横林看到的话,一定会高高兴兴地向季鹤模仿,但他很晚才看到,而且现在是很野心很大的坏家伙,于是他又用红笔把原本的句号划掉,在后面补了极工整的三个字——和爱人。
季鹤还没有很好地接受这个角色,他起先是回避的,因为给季君烧香时,有一根香怎么都点不着,季鹤以为是季君在生气。
季鹤记得他生前的每一句话,他告诉季君,他已经放乔横林去看世界了,乔横林连国外的风景都见识过了,可是还是愿意回来小浦书店,他也上过大学了,可是没有跟别的同学谈恋爱,他已经能够独立生活了,可是没有提过分居。
他也许是真的爱我,季鹤双手合十,跪在蒲团上,尽管口头上用了也许这样不确定的词汇,但又用了真的这样强调的语气。
季鹤一直以为乔横林是不知道这件事的,直到某天他起床发现身侧没有人,他走出卧室,看见昏暗的前厅里跪着一个大黑影。
“你怎么这样子,”乔横林委屈地说,甚至有些指责的意思,“我告诉你,就算是你阻拦,我也要跟他在一起的。”
说完,乔横林似乎觉得自己太冒犯了,他又把你替换成您,重新说了一遍,口气也从理直气壮变成了卑微乞求。
季鹤看到乔横林起身,立刻侧身躲了下,想要看他干什么去。
乔横林走到开水壶旁,把旁边的香抽出来一把,用火机一根一根地点上,不过还是有几根烧不起来,他噗通一下又跪了下去。
虔诚万分地求道:“求求你,让我爱爱他。”
他闭着眼睛时,季鹤夺走了他手里的香,用指甲碾断,原本应该是干爽的粉末粘连在一起。
季鹤无奈地揪住乔横林的耳朵:“你又把香搁在茶壶的柜子上了吗,水蒸气会让它们受潮的。”
乔横林顺着季鹤的力道站起身,又跑到收钱的柜台下面,翻出一把新的香,拆开塑料膜,抓了五六根,他用打火机一烧,不仅着了,还烧成一片,亮得不得了!
乔横林呲牙乐乐,赶紧跪下来冲着骨灰盒磕了好几个响头:“对不起,我冤枉您了。”
“快灭掉,好呛。”
季鹤捂住鼻子,乔横林连声答应,可就是转着圈躲着季鹤预备吹气的嘴巴,让香又烧了好大一会儿,充盈了整个屋子,他才勉强把他吹灭。
季鹤不得已把窗户打开,窗外桂花树的斜枝砰得一声,伸进了窗口,叶脉延伸出如水般的月光,仿佛滴在他身体上。
乔横林呆呆地站在原地,喉管情发地痉挛,他抿住嘴唇,向还没有完全习惯亲吻的季鹤说:
“我有点儿想跟你那个。”
季鹤不解地偏头,问:“哪个?”
乔横林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是修正了刚才的言辞:“我超想跟你那个。”
季鹤和乔横林天天睡在一起,却从没这么拘谨地躺在没有被子的床上,乔横林翻身坐起,扣住季鹤的腰,季鹤别扭地将脸偏向墙面,但很快又扭正回来,他伸出手,轻轻划过乔横林肩膀的纹身。
“疼不疼?”
乔横林摇摇头,他攥住季鹤的手腕,让他更加大胆用力,告诉他这是假的鹰。
季鹤认真抚摸时,乔横林发出了些别样的声音,季鹤耳朵垂立刻烧了起来:“你不要这样叫。”
乔横林捂住嘴巴,点点头,过了一会儿才垂着眉眼,告诉季鹤:“他们说,下面比较爽,我要当上面的。”
“不行,”季鹤拒绝,“我不想当下。面。”
乔横林只愣了几秒,就顺势躺了下去,他往上移了下身体,给个头不如自己高的季鹤找到合适的姿。势。
“那你来吧。”
一米九的大个子蜷。腿娇羞起来。
季鹤抿了抿唇,又提了提气,脸烧得通红,胸膛快憋得爆炸时,他终于叹息一声,挂在耳边的长发也因此垂头丧气,掉在乔横林的脖子上,痒痒的。
尽管可能会伤害到乔横林,但是季鹤还是坦诚地说:“其实我有点儿接受不了。”
“那还是我来。”
乔横林拍拍季鹤的胸脯,一副包在自己身上的样子,实际上他更紧张,埋着头比量了下位置,那谨慎的架势恨不得打个灯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