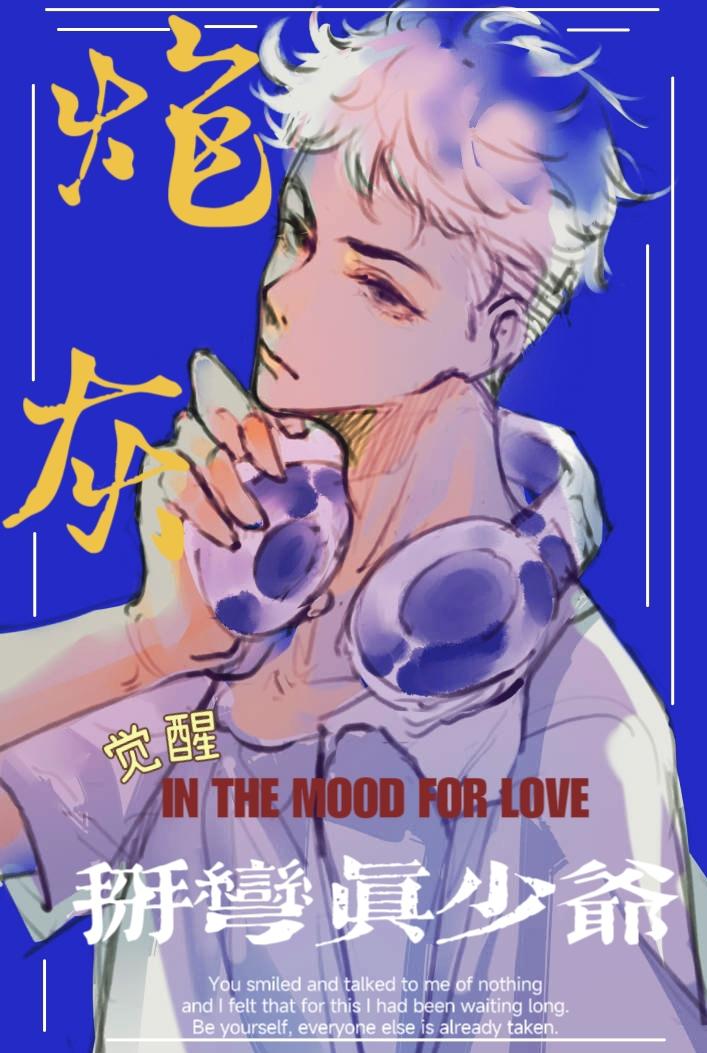笔趣小说>你瞒我瞒歌词 > 第93章(第1页)
第93章(第1页)
“不要去管别人说什么,你只需要做你自己就可以。”
“我知道。”·
回到教室的时候,余迢课桌上放了一张纸条,凑近查看——下课后到操场。
没有留名字,余迢也认不出字迹,他猜应该又是那群人,把纸条揉在手心拧做一团,转身往垃圾桶一丢——恰好落到一个alpha的脚边。路款冬。
余迢和他完全不熟,却对他莫名有些怵,说了句“不好意思”,走过去把纸团捡起来,站起身时,头碰到了他的胳膊。
奇怪,刚刚蹲下的时候不觉得路款冬离自己有这么近啊?
“又要说不好意思了。”路款冬突然开口,没等余迢回答,自顾回到自己的位置上。莫名其妙。·
操场这边其实有很多猫腻,只不过都被夜晚包容,平日教导主任抓的早恋,在这一逮一个准,特别是假期后。
任安晗帮着余迢,那群人没再敢对他动手,但喜欢干一些没证据的,拿他们没办法的事,比如造谣,造谣成本太低。
余迢有时候也不想见,一开始还会觉得不甘,后来就变成一种好奇心理,好奇他们还能在自己身上找到什么乐趣。
他一直对自己很无所谓,任安晗的出现才让他学会一点自爱。
“喂。”
声音有些熟悉,余迢怔愣片刻,路款冬映在自己的眼眸里。
“别再往前走了,是个草坑。”路款冬坐在石头上,双手随意搭在膝盖上,背低着,看人却有种压迫感。
“你把我叫来这的?”
“不然呢,还会有哪个alpha约你吗?都对你避之不及吧。”
这位同学说话刺刺的,他不喜欢,而且我们很熟吗,余迢纳闷,“没什么事我就走了。”
“别人说你,就要反击啊,”路款冬没让他停住脚步,知道他听到这句话就不会走似的,悠悠道,“你不会认为自己退让对方会觉得你无聊,没意思吧?”
余迢果真没继续向前,说:“我不是退让。”
“我是懒得理,越理越起劲。”
黑夜里的月光寡淡,轻轻地盖在路款冬身上,余迢觉得月光和太阳都是很公平的,落在每个人身上都不会特意关照谁,将某人衬托得别致,除非,那个人本身就很耀眼。
余迢这时候才发现,除了任安晗,他很少和人有超过十秒以上的眼神接触,那些欺负他的也好,与他谈话的也好,余迢总是下意识避开。
第一次注意到路款冬的眼睛,余迢的心跳声没由来的变重了,这感觉就如过山车达到最顶峰,坐在后排的你不知道何时下落,在某个时刻突然袭击——这是很漂亮的一双眼睛。
有点熟悉,一时间联想不到,也许是夜色实在太暗了,将一切都朦胧,包括思绪。
“你为什么把我叫到这里,就为了和我说这些吗?”
“那我还没那么无聊,”路款冬站起来,眼底的波光涌动消失不见,月光游曳到他的肩角,“之前从你面前经过,我说信,是随口一说。”
“就这事,没了。”路款冬转身得很干脆。
“什么?”余迢没听懂,想再问问,脚动不了,像被粘在原地。
再抬头,眼前如电影转场,余迢身处晕目的漩涡中,路款冬的背影慢慢变得遥远,但并不模糊,余迢发现,自己可以走动了。
伸手去够“背影”的肩膀,那人转身,余迢的眼睛里映着的却是任安晗。
他身上都是伤,玻璃从胸前贯入后背,胳膊上布满血渍,身上的衣服变得湿哒哒的,不断有袖扣滴出沾染了鲜血的水。
这看上去像是任安晗车祸后出走的灵魂,肉体在手术室里抢救。
可此时此刻的余迢并不知道任安晗为什么会变成这副模样,惊吓着叫出声:“学长、你,你怎么了?你哪里痛吗?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谁欺负你了?我、我带你去医院好不好?”
任安晗看上去不像受了重伤的样子,谈吐很稳:“不用。”
“我要走了,余迢。”
“啊?去哪?你这个样子要去哪?很危险的——”
“不是,我现在依附于你的记忆,可能马上,你就会忘了我吧。”
“我怎么会?”余迢急得要死,“你先跟我走,去医院好吗?”
“但是这是我希望的,我不希望你一直记着我,”任安晗释然地笑了声,“真的。”]
“哥哥……醒醒,”秦最轻轻拍他的脸,见他又做噩梦了,听医生的话,狠下心掐了他一下,“醒醒,余迢。”
余迢睁开眼,这样的天气里居然流了一头的汗,大口喘着气:“别走——”
秦最被他抓住胳膊,呆滞:“我、我不走。”
意识到方才看见的全是虚幻,余迢骤然放松,坐起来:“对不起,我……”
“安晗是谁?”秦最想转移他注意力,问,“看你刚才一直叫他的名字,还有路款冬的。”
“是么,”余迢避重就轻地回复,“我们……什么时候离开这里去a市啊。”
这两天因为余迢变成oga情绪不稳定,秦最都没敢提出来,怕他善变,指不定反悔了。所以秦最现在听到这话很高兴,“今天就走。”
“哥哥,谢谢你愿意给我机会。”
余迢疲惫地笑了下:“我真的没心思去喜欢谁了,不用在我身上浪费时间,是我该谢谢你,等到了a市,你就回来念书吧……遇到更好的人——”
“你还有什么要带的吗?我去理理。”秦最截口打断了余迢的话。
知道他是不乐意听,余迢也懒得照顾他的情绪了,总之自己已经明确过意思,那么秦最选择怎么做和他也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