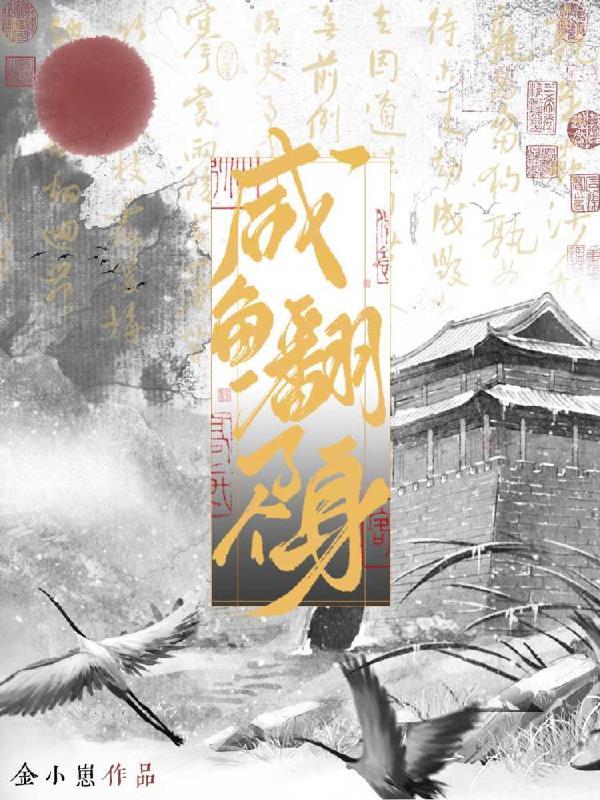笔趣小说>铁衣披雪番外全文免费笔趣阁 > 第15章(第1页)
第15章(第1页)
“危家寨穷成这样,多半并不知道刀里藏着的事,姑娘要不直接跟危大当家提一提?”见岑雪担心刀已被危怀风扔掉,夏花也有些不安。当年老爷做事不留余地,危家人嫌那把刀碍眼,一气之下扔掉也不是没有可能。
退一步说,就算没扔,危家寨陈放兵器的地方那样多,这要是找起来,也不知要花费多少功夫。
“不可。”岑雪仍是摇头,“正是因为危家寨穷,才不能贸然提起刀的事。”
夏花再次沉默。
岑雪见两个丫鬟都有些垂头丧气,提起精神,道:“没关系,再找找看吧。我刚刚说笑的,危家人不会糟蹋圣物,刀应该就在寨子里。”
夏花、春草知道这是在安慰她们,百感交集。春草说道:“我看危家人对姑娘的态度也还不错,没有因为昔日的事为难报复,想来危大当家为人磊落,姑娘再与他处上一段时日,定能找到些线索的。”
这是反过来宽她的心,岑雪点头,想起危怀风,心底又有一丝顾虑浮起:“也别只想着刀的事了,三日后,寨里大婚,四方八寨的人都要来赴宴,我谎称被裴大磊劫持胁迫一事,怕是瞒不住了,届时他们若问起,便说遭遇贼匪不假,是那帮贼人假借裴大磊名号,可记住了?”
那天上山,为尽量说服危怀风,岑雪撒谎是受裴大磊胁迫,本以为危、裴两家有旧仇,这戏短时间内不会被戳破,谁知道危家寨竟然要邀请裴家寨来喝喜酒。
春草、夏花两人皆一愣,知道这事情重要,连忙应下。
※
林况在会客厅里承诺三日后举办婚礼,果不其然,不出两日,寨里便已张灯结彩,放眼望去全是一大片喜庆的红。
这两天,岑雪这边也没闲过,撇去准备婚礼一应用品的事情不论,光是客人,便接待了足足六波。
别看危家寨不大,成家的人也不算多,女眷却齐全得很,一来便来一整家,上下至少三代,说起话来,耳朵根本就没有得闲的时候。
其中,最能说的还要数林况的夫人孙氏,说话爽利,性情开朗泼辣,一开嗓便能说上半个时辰,一壶茶都不够她一人喝。
其次,便是周俊生的母亲苏氏最热情,虽然不算爱说话,但是每日都要来,早晚各一次。要么是陪岑雪看看花,吹吹风;要么就提一盒新鲜的糕点来,请岑雪一块品尝。
除此以外,寨里还有不少和危怀风关系亲近的人来过,大多是些年长的阿奶、阿婶,或是一群叽叽喳喳的娃娃。大家来的时候从不空手,有送吃食的,有送香囊、手帕的,也有小女孩从田间来,送上一大捧五颜六色的蓝蓟花、打碗花。
才两日,岑雪屋里便快被堆满了。
大婚当天,天没亮,岑雪被屋外的动静吵醒,唤春草进来一问,才知道是寨里的阿奶、婶婶们来了,说是跟着孙氏、苏氏一道,过来给新娘子洗漱更衣,梳发开脸。
岑雪赶紧起床,等人进来后,坐在梳妆台前。孙氏、苏氏帮忙梳妆。
“哎呀,怪不得怀风这么些年都不正眼瞧别的姑娘一下,有这样美的小青梅在,还能看得上哪家姑娘?”孙氏端详着镜子里的岑雪,越看越震撼,开嗓夸赞个不停。
众人跟着附和,眼睛盯着妆成的新娘,不舍得挪。
“阿雪,你不知道,这些年来,山底下觊觎怀风的姑娘就跟那水边的芦草似的,唰唰地长,一年比一年多,可他偏就是一个都看不上。我原先还想着,到底要个怎样的仙女才能把他给收了,见着你,可算是服气喽!”
“阿雪姐姐真美,比仙女还美呢!”
“是,是,一会儿你怀风叔叔就要娶仙女了!”
众人的夸赞不绝于耳,岑雪看着镜中凤冠霞帔、朱颜绿鬓的自己,突然生出一点当真要跟危怀风成亲的错觉。
“阿雪,你说说,怀风以前是不是答应过你,除你以外不娶旁的姑娘呀?”孙氏又凑过来起哄。
岑雪赧然,低声道:“没有……”
孙氏“啧”一声:“那就是他心里头对你念念不忘,得亏是你来了,不然这臭小子还不得打一辈子光棍呀!”
岑雪的脸越来越红,低下头来,在旁人眼里更是娇羞得惹人怜爱,笑声盈满屋舍。
黄昏时,婚礼开始,岑雪拿上喜扇,挡在面前,被孙氏、苏氏领着离开屋舍,前往会客厅拜堂。
危怀风已等在屋外,穿着一身红,束发用的是红绸带,马尾仍旧散着,使他看起来不像个成熟的新郎官,倒更像个“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少年郎。
见岑雪被众人领出来,危怀风把手里的一截红绸递过去,岑雪接住,在大家的起哄声里跟着他往前走。
“同你说了什么?脸红成这样。”危怀风打开话匣子,声音不高不低,恰巧是二人能听见、旁人听不清的程度。
岑雪想起先前在屋里的遭遇,有些羞窘,道:“说大当家是不是答应过我,除我以外,不娶旁的姑娘。”
危怀风失笑,道:“还有呢?”
“得亏是我来了,不然大当家就得打一辈子光棍了。”
危怀风转头看过来,目光落在岑雪娇红的、有点婴儿肥的脸颊上,低笑一声:“那可真是多谢你了。”
岑雪抿唇,不再做声。危怀风的笑有种魔力,总是让人心乱。
不多时,会客厅到了。
孙氏说,确定吉日后,林况便派人把请柬发了出去,今日来喝喜酒的客人少说也有一百位,算上寨里的五百人来人,场面可以说是盛况空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