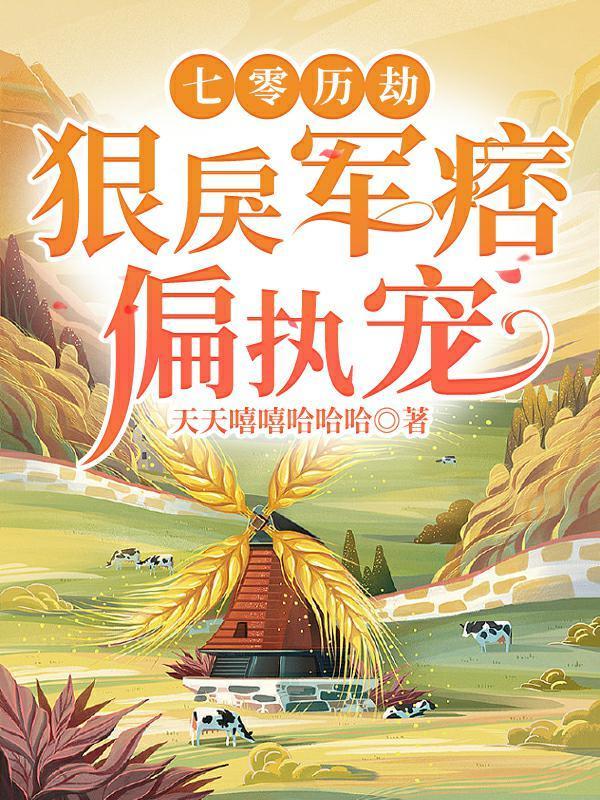笔趣小说>光棍村的婚礼 > 第11章 老支书收留遇难女(第2页)
第11章 老支书收留遇难女(第2页)
“当他知道我是被遗弃的孩子后,他待我像亲哥哥似的,叫我干妹妹,去年替我教训过胖鸽子,说要再欺负我,他就劈了他。”
“还有这样的人?”夫人问支书。支书点点头,没吱声。
“贼所长知道后要给小舅子出气,准备找“刀疤”算账,一打听刀疤在县局里有一帮弟兄,贼所长没了脾气,不敢动刀疤。”
“世上总有仗义的人,这就叫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支书自言自语的说。
夫人说:“黑吃红,红享黑,这黑红不分,是不是世道变了。”
“嗯,接着听春梅说。”
“贼所长没敢动刀疤,但并没有放过我,他三番五次的让歪脖子给我捎信,提出来一月给我一千元,不让我在唱歌,专心做他的小老婆。”
“混账东西,那不是胡说八道吗。”支书气愤的骂道。
“有一次他喝醉酒,动手动脚的调戏我,让我挖破了脸,那次他打了我。”
我想告诉“刀疤”,又不敢,怕“刀疤”闹出人命来,更怕“刀疤”被所长伤害。
“你和刀疤啥关系,闺女,他对你是不是有意,给大伯说实话。”
“刀疤是个正人君子,多为人善抱不平,仗义疏财干净的很,从不近女色。”
夫人说:“世上还有这么好的人”
“额今天发生什么事了,让大伯来帮你?”
“昨天晚上,我在红光歌舞厅唱歌时,看到胖鸽子和歪脖子调戏一个女孩,那女孩是歌厅的陪酒女郎,被胖鸽子灌得烂醉,歪脖子乱摸乱亲那女孩,胖鸽子扒下女孩的裤子,就往包间拖。”
“流氓,世道怎么变成这样了老李。”夫人牙咬的咯咯响。
老支书呼吸急促起来。
“我去告诉歌厅的老板,老板说惹不起不要我管。”
“丧尽天良了,老板都管不了,你就别管了闺女。”夫人叹口气说。
“这女孩很苦,老母亲下肢瘫痪,卧床三年了,全靠她打工挣钱养家。我想让刀疤哥帮她,但刀疤在县城一直没回来。”
“后来呢?”支书问。
“我喊了两个陪酒女,拿着啤酒瓶悄悄的溜进包房去,两个畜生正准备对女孩下手,一看我们进来了,提上裤子就往外跑,胖子回头说我:“够了,你就等着吧’。”
“后来有个公司老板点我的歌,我去了他的包间,站在门口朝里伸头看了看,贼所长坐在沙发上,怀抱着一个女孩正亲吻乱摸呢。那女孩两腿蹬地,拼命的挣扎着,包间里弥漫着淫乱的狂笑声,我感觉不对,立马退出去,离开歌舞厅。”
“这乱七八糟的地方咱能不去吗孩子,再也不要去了。”夫人生气的说春梅。
“我离开舞厅遇到了几个姐妹,喝了一夜酒,要分手时华姐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姓贼的在歌舞厅翻箱倒柜的找春梅,没找到带着六个警察去光棍村了。”
华姐问打电话的人:“为啥要抓张春梅?”
“有人说春梅参与卖淫活动,听说是个男嫖客咬出来的,稀罕事,男人嫖娼咬出女人来。”
华姐挂了电话,问我到底有没有这种事?
“诬陷!诬陷!”我心都气炸了,牙齿咬得咯咯响。
她们劝我快出去躲躲,免的麻烦。
我沿小路走回村子里,快到村口时看到警车进村了,没拉警笛是悄悄去的。
我偷偷的躲在家后的水沟里,看到车子停在门口,后来门口围住好多人。
我心跳得厉害不敢回家去,就来找您了。
听完春梅的叙述,老支书脸色铁青,额角的青筋暴跳,搓着手在床前来回走动。
“无法无天了,这哪里是共产党的公安,腐败!畜生!共产党的败类!”支书气的发抖。
夫人满眼含泪,紧紧地把春梅抱在怀里,唯恐被人抢去。春梅喘着粗气在夫人的怀里又“哇哇地哭起来。”
夫人说:“可怜的孩子,因生活所迫受尽世间的欺凌,尽情地哭吧,哭也是一种宣泄,天大的委屈,哭出来就好。”
“从现在开始,春梅哪里都不要去,就在大伯家里住着,看谁敢来抓你。”
可怜的张春梅,这里是你的久留之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