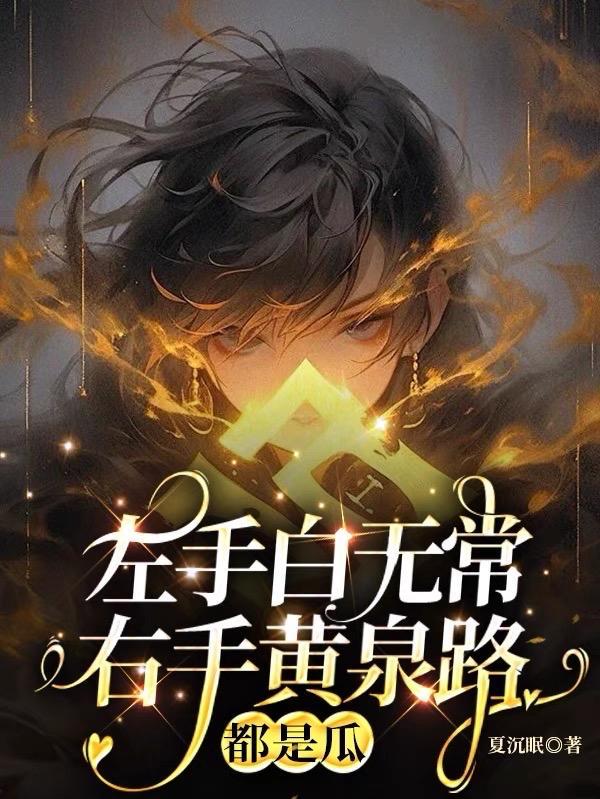笔趣小说>蜗牛与玫瑰树续写 > 第18页(第2页)
第18页(第2页)
倏地,露出一截白皙柔软的脖颈,微微瑟缩了一下后,时初又惊慌失措地赶紧抓起帽子,把自己挡住。
小刺猬不仅在躲着什么,也把浑身的刺儿竖起来了。
沈淮年垂着眼,抿着唇默不作声地望着她。
看着她恨不得有隐身术的模样,心中也难受的厉害。
这比他在公交上见到她时还要严重。
严重到让他不知道如何伸出手去摸摸她的小触角。
停顿了很久,沈淮年直接站起,把椅子拿到过道上,给自己腾出更大的空间,然后蹲下身,仰头,慢慢地,一步一步地,怕打草惊蛇地往时初的方向小挪几步。
他见到时初明显战栗了一下,忽然有些不敢往前了。
墙角的花朵偷听了一天的课,这会儿日薄西山,也精疲力尽,懒洋洋地伸了个懒腰,又互相簇拥着准备入眠。
“时初。”
到最后,他还是叫她了。
嗓音沙哑低沉,透着点扣入心弦的心疼。
像在试着和襁褓里的婴儿交流。
渴望她能给自己一点回应,又很明白她很可能不会应他。
他猜到她在哭,可总不好像刺一样什么都不管不顾地逼问,沈淮年尽可能地不让她感到害怕,故意扯开话题,放柔声音,“困了的话回宿舍去睡,趴在这里容易感冒。”
他真的是有副上天赏吃饭的好嗓子,容易让人卸下防备。
听到熟悉的声音。
时初当即懵住,大脑一片空白。
有那么一瞬间,是想躲起来不让沈淮年看到自己是怎么狼狈的,只是,思维还跟不上行动。
在沈淮年第二次喊她名字的时候,她就像牵线木偶般顺着那声“时初”下意识地抬起头。
视线微微往下,看向沈淮年。
刷子般的被沾湿了的眼睫轻轻耷着,眼眶红地和兔子眼睛似的,眼角还噙着泪花儿。
像被人欺负了的小孩,可怜巴巴的。
沈淮年怔住。
心里咯噔一声,也跟着难受,难受极了。
慌乱在眼中一闪而过,他下意识地舔舔唇,有点不知所措。
怎么了?是真的被欺负了吗?还是老师上课说她了?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
对望片刻,在时初快要接受不了这种注视想退缩把自己藏起来的时候,沈淮年突然伸出手。
动作快到令时初躲闪不及。
大拇指指腹轻轻在她泛红的眼梢刮过,刮走那抹湿润。
沈淮年声音更加低哑:“谁欺负你了吗?”
时初瑟缩着往后贴了贴。
埋着脸摇摇头。
触感似乎还停留在眼角处,像被烈焰烧过一样,让她瞬间忘却了呼吸,屏息到差点窒息。
察觉到沈淮年的手掌还贴在自己脸颊附近,时初抿抿唇,条件反射性地想要别开脸。
沈淮年察觉到她的意图。
眉梢一动,识时务地收回手,“抱歉。”
也没有那么严重到需要道歉的地步……
时初情绪稳定不少后,对听到他的“抱歉”也感到如坐针毡,她咬咬唇,想说“不用”的。
只是当她闷着声儿准备说话时,沈淮年打断了她。
“抱歉,我应该用纸巾的。”沈淮年说。
时初:“………”
然后,他站起身,拿起搁在桌上的一小包纸巾,抽出一张抬手,替她擦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