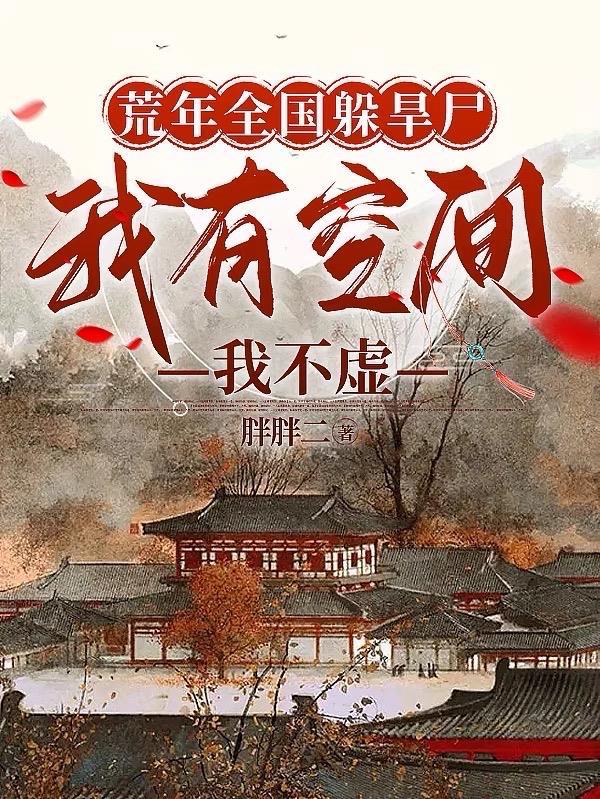笔趣小说>太阳底下by流光岁月 > 第7章(第1页)
第7章(第1页)
伊明每每想到他们导师的笑,就会激灵灵打个冷颤。
如此一来,伊明就把大量精力放在了论文上。而每晚10点锺,李云歌会准时打电话来。伊明有时候会接完电话继续奋战。毕竟,深夜的校园安静得很,而且这段时间没有任何事情会来打扰。或者,用他们楼里头那些夜猫子的说法,这是一段完整的时间,没有国际流行的碎片化,适合用来做学问。伊明就这样慢慢地养成了日夜颠倒的习惯,开始和不少人一起过美国时间。
慢慢地,早晨从中午开始就形成了习惯。
这麽著过了一个多月,伊明所收集的资料也差不多了,对资料的整理笔记也做了有3万字余。大纲拟了出来,导师过目之後,说不错,有主线,有逻辑。
这话就他们导师而言,那已经算得上是不小的夸赞了。伊明得意之下,就和另外几个虽然不是美国公民却过著美国时间的家夥,通宵斗地主。
斗至天将熹微时,那个额头通红(被弹的)的地主打了个冷战,骂了句,直娘贼,连老天都跟著欺负本老爷。而後从对面小贫农的床上拉了毯子裹了裹。
天亮时,果然降温降了10°之多。除了那个裹了毯子的地主,午饭之前,其他人都光荣病倒。头疼,流涕,喉咙沙哑,全身酸软,伴有体温明显升高。於是没有病倒的地主开始轮流伺候几位贫农喝药喝水。边伺候,边高唱社会主义好。
病倒了的小贫农笑眯眯地摸著地主的头,“有觉悟,有前途。晚上去打地瓜稀饭,还要乌江榨菜,榨菜要榨菜丝,不要榨菜片。”
地主一边摇头一边感慨,“三座大山,三座大山,我要穿越回封建时代!”手里则老老实实地拿了三个人的饭盒去排队打稀饭。
吃了晚饭的三位贫农,指示地主老爷继续奉药奉水,药是白加黑,水是顶滚的开水。然後出门替哥儿几个踅摸个片子回来看。地主老爷出门之後,这仨贫农在这一次该喝白片还是黑片的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
小陆同学和另一个贫农认为既然人家是两个白的配一个黑的,那显然是早上、中午喝白的,现在晚上了麽,当然要喝黑的。
笑眯眯的小贫农认为,人家这麽配是给过北京时间的人参考用的,对於他们这些过华盛顿时间的,当然现在应该喝白片。
正要以23多数决通过时,地主老爷回来了,地主老爷当然无条件支持小贫农,居然形成了2:2的僵局。
小陆同学和另一个贫农一致认定,地主老爷的政治权力应该受到限制,故而他的那一票不能成为完整的一票。
几个发烧烧昏了头的法学硕士候选人,为了吃药的问题居然争论了将近一个小时。等都消停下来之後,地主老爷打开了电脑开始放片子。
很老的片子,《霸王别姬》。看著程蝶衣在里头风华绝代的扮相和表演,看著程蝶衣在里头坚持一辈子就是一辈子,少一分一秒都不行,看著程蝶衣在里头用手圈住段小楼的腰,问著这儿,这儿,这儿……
手指一寸一寸的移动,生生成就一幅暗香浮动的画。
片子看完,已经快要11点了。
地主老爷长吁一声,我不见人生而自由,却只见他无处不在枷锁之中。
另一个贫农说,这个世界把人逼得变态,却又容不得人变态。
小陆同学沈默著。
小贫农一脸红红的,垂著眼,窝在床铺上,一言不发。地主老爷偶尔偷眼瞧瞧,看人不理会自己,拎了三个水壶下楼打开水去了。边走边唱“状告当朝驸马郎,欺君王,藐皇上,悔婚男儿招东床……”
李云歌从10点锺开始打电话,宿舍座机,手机都一直没人接。眼看过了10点半,仍然联系不到人。李云歌坐不住了,拿了外套,边往外走边打电话给杜云辉。
交待了公司的事情,李云歌发动了车子出门。眼看快要到高速公路的收费站时,电话响了。来电显示是陆伊明。李云歌急忙把车子靠边停下,接通了电话,那边传来陆伊明明显心虚的声音,“阿哥,那个……我在同学那儿,手机没有带……”
李云歌长长地呼了口气,用手揉了揉眉头,“我还以为你什麽事儿呢?”李云歌就这样静静地坐在车里头,“伊明,你声音怎麽听起来不大对?”
“哦,降温,感冒了!”
李云歌想了想,还是发动了车子,往收费站开过去。“吃药了麽?”
“嗯,吃过了!”
“那早点睡吧,生病的时候要多休息。”
挂断了电话,李云歌也上了高速。
早上8点半,李云歌出现在伊明宿舍楼下。李云歌掏出手机拨了伊明的电话,没有等到接通,李云歌就挂断了。然後上楼找人。
李云歌敲门敲了好几次,力道也加重了些,但门里边还是没什麽回应。这时,旁边宿舍走出来一个男生,揉著惺忪睡眼说道:“伊明这夜猫子这会儿肯定还在睡,你还是午饭过後再来吧。”
李云歌先是愣了下,然後对那个男生笑道:“伊明一直熬夜?”
“哦,要毕业了,大家都是这样。”那男生讲完话,就又回去了。
八
中午快要12点半时,伊明醒了过来。洗漱完,准备再去奴役下地主老爷。
拿了饭盒刚出门,就听到走廊传来一阵熟悉的笑声。伊明想,不是吧。走到隔壁地主和小贫农的房间一看,背对著门口坐的那个人不是李云歌是谁。
伊明一下子有被人抓现行的心虚胆怯,耳边是每晚11点结束电话时,李云歌低缓温柔的声音,快去睡觉,乖,别熬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