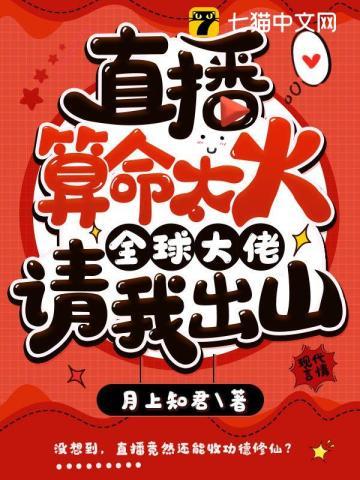笔趣小说>红糖鸡蛋西西特 > 第 1 章我做梦都想当Omega (第1页)
第 1 章我做梦都想当Omega (第1页)
深秋的雨淋在一片片灰瓦上面,顺着瓦片的弧度往下淌,出劈里啪啦声响。
地面被一滴滴雨水砸成了泥。
村子西边,一户门前摆着张小竹椅,手长脚长的年轻人以别扭的姿势窝在上面打盹。
光秃秃的桃树枝丫拦不住秋风,眼睁睁看它扑向乌长颈的年轻人,钻进他解开两颗的花衬衫领子里,吹开他西裤的裤腿,贴上他瘦白脚踝。
夹着雨的风很大,吹得他半长头凌乱,衣裤抖动,单薄清瘦的线条若隐若现,有种易碎的美感。
有两串脚步声由远及近,是张家的母子二人,他们披着雨衣戴大斗笠帽,要去田里通水沟,脚上的脏胶靴踩过腐叶,泥水乱溅。
“烦死了,又下雨没完了还”小张狠狠剁了一下桃树。
竹椅里的年轻人睁开眼。
他的睫毛天生就很密很黑,像画了精致的眼线,瞳孔深黑,丰满微湿的唇红润,如饮过鲜血涂过胭脂,搭在身前的十指白得光,一张脸媚而不显女气。
仿佛一只来人间作乱的画中妖。
隔着雨幕扫来的那一眼,宛如情人的缠绵。
小张看呆了。
“下不下雨不是我家那桃树决定的,它挨你一脚,多无辜啊。”年轻人说话懒懒散散,有股子勾人的味道。
小张两眼直,不停吞咽口水,魂都要没了。
张母拽住尚未分化的稚嫩儿子,抓紧手中铁锹冲屋檐下的beta吼“梁白玉”
梁白玉坐起来点,上半身前倾,秋雨斜飞到他优柔的脸上,打湿他左手腕部的咖啡色膏药贴,他一双眼生得太好,含着几世的情般“小嫂子叫我呀。”
张母板着脸,瞪吃人不吐骨头的魑魅魍魉一样,戒备又厌恨地瞪了他一眼,强行拽着自家不成器的儿子离开。
梁白玉笑嘻嘻的窝回竹椅里。
竹椅的岁数不小了,不能轻松承受他的重量,出了闷闷的声响,又没了。
雨还在下。
斜对面那家,不知看了多久的刘婶朝雨里啐一口“狐狸精”
“奶奶,什么是狐狸精呀”小孙儿天真可爱。
“会被天打雷劈的祸害”关门声里夹着刘婶的骂声。
“轰隆”
天边裂出一条长长的白线,雷声炸响。
梁白玉掀眼皮,望了望湿沉沉的天“你也凑热闹。”
一道闪电劈下,梁白玉撇着嘴站起身“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回了回了。”他拎了竹椅进门。
雨一直在下,天暗得早,还停电了,村里湿哒哒的,没人出来走动,各家都点起了蜡烛。
近十年,村里66续续摆脱土房,瓦屋土基房,建起平房,条件好的更是盖了两层楼房,只有梁白玉家还是老屋。他自己和他家都像是被村子屏蔽在外。
但这种不相容的原因不同。
他家是停留在了过去的时光里,没跟上同村人前进的脚步。
而他自身刚好相反,是他先其他人一步甩开了这个村子的陈腐味,他无拘无束,没有活在哪个框子里。
小半截蜡烛立在桌上,烛火摇曳。梁白玉掰开硬邦邦的馒头,把一半放进碗中,倒进去一些开水。
馒头很快就软了烂了,散着淡淡的老面香,他从筷子筒里捞出木勺,挖点白糖洒在馒头上。
木勺有些年头了,前头几处长了洗不掉的黑斑,有几粒碎糖粘在上面,被他一点点吮掉。
有一滴微凉的液体落到梁白玉头上,渗进丝,他一抬头,眼皮上也砸了一滴。
屋顶湿了好大一块。
梁白玉见怪不怪的拿了个盆放地上,接雨水。
家里的几间房都在漏雨,滴滴答答的掉在盆里,盆有限,有的地儿都没东西接,直接滴下来,地面都泥糊糊的。
墙壁上也渗出一条条的水痕。
“滴答”“滴答”
屋里屋外都在下雨。
梁白玉看着瓷盆里褪色模糊的“红双喜”字迹,看它被一滴两滴的雨覆盖,他一勺一勺的吃着烂甜馒头,心里愁,一场冬雪下来,房顶怕是要塌,根本撑不到明年春天。
老屋该修了。
吃完馒头,梁白玉从裤兜里摸出一块老旧手表,细细摸了摸布满长短划痕的表盘,勉强辨认出了时间。
快八点了,这个僻静偏远的村子已经打起了无形的哈欠,昏昏入睡。
梁白玉没有胶靴,他就踩着回家那天穿的的浅棕色皮鞋出了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