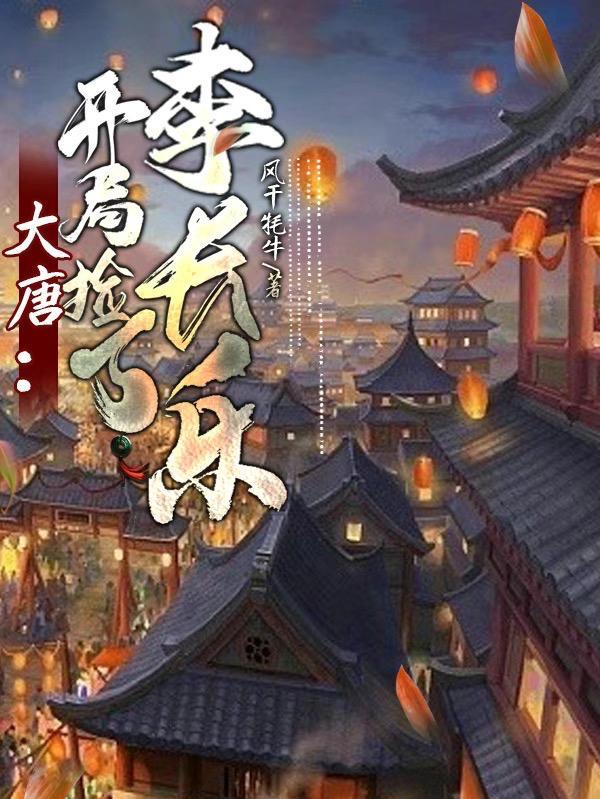笔趣小说>冷戾摄政王的小甜娇免费阅读 > 第157章 这其中一定有什么秘密(第1页)
第157章 这其中一定有什么秘密(第1页)
“母后,究竟生了何事,朕一听说寿康宫出事便紧接着赶过来了!”
景元承言语恳切,全是关心之意。
可从紫宸殿到寿康宫,这么远的距离,刚刚出事之后,圣上就算能第一时间得到消息,疾步快走也是来不及的。
岳太后心里盘算一番,视线暗暗在门外一众下人身上扫过。
不知哪个是她殿里的小耳朵。
片刻,她由景元承搀扶着在主位坐下,“无事,圣上放心吧,只不过是生了一点意外。”
视线看向谢长宴,才道,“今日你们可是在议论政事,不要因为哀家的这点小事耽误了,快些回去吧!”
岳太后越是这样说,景元承心中更加不放心。
“母后的事,哪有小事,作儿臣的,政务繁忙本就疏于尽孝,如今母后殿中出事,儿臣再不来,岂不是让天下人耻笑。”
如此说着,景元承的眼神不动声色的在几人身上扫视。
孟知溪感受到打量的视线,垂着眼,面色坦然。
但她的手指,还是将谢长宴微微攥紧。
刚刚细看,谢长宴的眉眼确实和圣上有几分相似,而这一点相似之处,全随了太后。
孟知溪越想越感觉心惊,甚至感觉这把剑就悬在头上,随时能落下要了谢长宴的命。
谢长宴感受到她今日的不同,握住她冰凉的小手,揉了揉。
“放心,一切有我在。”
今日气氛不同寻常,谢长宴是能感受到的。
就连往日最爱开玩笑的和宁,也面露愁容。
还有沈嵘,刚刚给他的眼色,大概是提醒他小心,谨慎的意思。
两人刚说了一句悄悄话,就听到圣上惊呼。
“母后,这伤是如何弄的,快来人传太医。”
岳太后刚刚已经擦了血迹,簪子划伤的小口子不明显,没想到还是被圣上看到。
“无碍,不必麻烦了。”
岳太后见隐瞒无望,也只能半遮半掩说出了谢侯怒极行刺的实情。
“岂有此理,谢大人,此事兹事体大,谢侯又是你家父,你如何看。”
孟知溪跟着心中一紧,但好在太后娘娘未提及当年秘事,想来,她也是想护着谢长宴一条命的。
谢长宴跪地,“请圣上恕罪,请太后娘娘恕罪,家父早已患了疯病,行为失常多日,臣一直隐瞒至此,是臣之过,该杀该罚,臣亦该担之。”
景元承见地上跪着之人,思虑良久。
如今政局,不能没有谢长宴,如此,今日之事,也只能重重提起,轻轻放下。
岳太后也跟着说道,“今日也怪哀家,不知情况,念着往日和阿姐的情分,想宣旧人入宫见上一面,谁想到……”
挥了挥手,她哀叹道,“算了,谢侯有错,亦是为景家的江山操劳了大半辈子,既然是疯病,那就灌些药去,封了嘴巴,卸了力气,押回天阳,好好将养着。”
这样的处罚,对于谢侯已经是从轻处置了。
谢长宴和孟知溪只有谢恩的份。
两人从宫里出来,谢长宴看她的小脸还是煞白。
手覆上她额头,量了量,才问道,“怎么了,今日是不是吓到了,都怪我,没有早点交代好他的事,害的夫人也跟着受牵连。”
孟知溪摇了摇头,正想说些什么,又惊觉,现在不是说话的好时候。
回到谢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