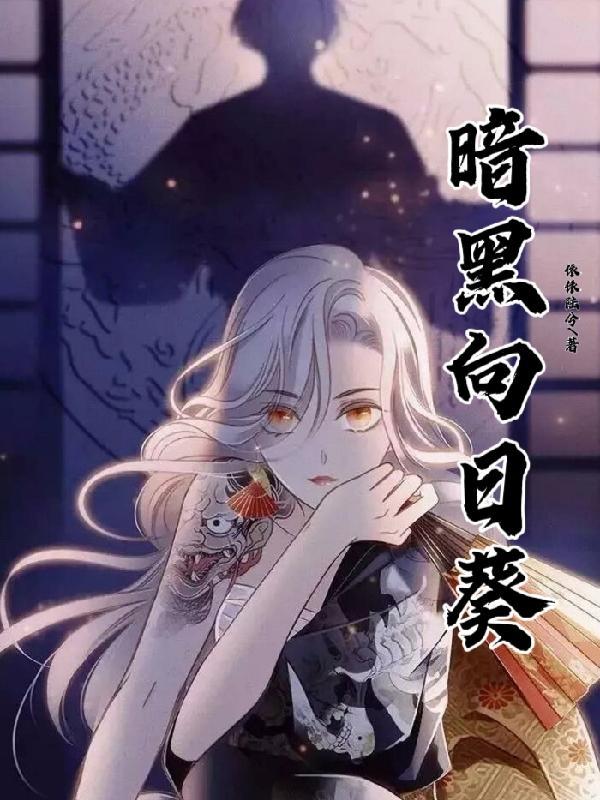笔趣小说>白昼之雨百度百科 > 真实面目(第2页)
真实面目(第2页)
朱利安不耐烦地啧了一声,没经验的年轻人让他觉得很烦躁。他说:“那就记住一件事情:在海上,要多听多看,但是,不要多问多想。”他冷峻的目光中带着些许警告,“别去理会那些与你无关的事情。”
肯连忙说记住了。
杜尔米却问:“可是,如果那些事情波及到我了怎么办?”
气氛骤然凝结。
朱利安又皱起眉。
劳伦特却笑了一声,他温声细语地说:“要么,获得能够与之对抗的力量;要么,就此认命,束手就擒。”
杜尔米惊讶地说:“只能这样吗?”
“只能这样,小鬼。”朱利安回答。他有点不喜杜尔米的性格了,这年轻人不敬权威、不敬未知。在海上,这种性格会带来未知的风险。
每一个航行在森罗海之上的船长,都恨不得自己招收的水手全是木讷呆滞的木偶。
……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样的性格或许更适合去追求力量。
朱利安深深地看了杜尔米一眼,随后说起了出航的日期。这显然也是劳伦特·霍索恩的来意。
他已经选定了下个月,丰收之月的第三天。
他用一种非常普通的、平静的语气说:“某位星群的信徒说,那天会是个好天气。”
“海沃德?”劳伦特笑了起来,看来是他的熟人,“您可以相信他的推测,在天文学这方面,利文斯通的其他信众都敌不过他。当然了,只是在信众这个层面。”
“但我们可没法让更高层次的大人物为我们预报天气,海沃德已经是个好脾气了。”朱利安摇了摇头,不置可否地说。
劳伦特轻声叹息说:“或许是太好脾气了。”
信众。杜尔米则注意到这个词。
听起来也是个力量的阶层,与先前听闻的选民一样;似乎要比选民低一些。毕竟信众还只是“众”,而选民就已经是“被选中”的了。
在奈廷格尔的森罗协会,肯·林恩跟着那位讲解员离开又回来之后,他曾经说,“他们说我不可能成为海镜的信众”。
……所以,信众就像是力量的第一阶段?最初阶层?
至于比信众更低的——见习,不是吗?
见习、信众、选民。
见习还只是最初的接触,信众似乎就已经登堂入室了。至于选民,那好像已经是寻常人没法接触的大人物了。
这么一说,力量的划分可谓是相当简单,甚至过于粗陋了。
“你们可以离开了。出航之前我会给你们送信,让你们提前去船上熟悉一下。”朱利安对三名学徒说,“把你们的地址告诉我。”
他们都说了。
值得一提的是,迈尔斯住在利文斯通市中心的一家酒店,听起来相当奢华。这样的人居然愿意去船上吃苦头,做个默默无闻的水手学徒,真是令人相当惊讶。
劳伦特都有点感兴趣地看了看迈尔斯。
不过朱利安仍旧面不改色,好似森罗海上的风浪已经浇筑了他的五官,让他面对什么都无动于衷。
三名学徒便离开了。
劳伦特在这儿与朱利安交谈了一阵,他也是第一次出海,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提前跟这位老船长请教一下。临近中午的时候,他才与朱利安告别。
他独自一人行走在通往港口的路上,最后来到海边站了一会儿。他缓慢地呼吸着,让那种冰凉的、沉静的感觉渗进胸口,缓解着一直以来的焦躁。
在利文斯通的所有信徒之中,劳伦特·霍索恩都可以说是一个天才。在他十岁的时候,他就已经摸到了力量的门槛;一年之后,他就已经成为一名信众了。
可信众与选民之间的距离,却仿若天堑。
他花费了十二年,多方打听,才最终确定了进阶的办法。
他微微闭了闭眼睛,然后又睁开。
“吾神,我将聆听您的告诫。”他用力握住胸口的书册挂饰,“我将在这段历史上,铭记我的姓名。”
下午的时候,肯才想起来他们忘了一件事情。
肯惊呼:“杜尔米,我们把水手证落在邓莫尔船长那儿了!”
如果要出海,他们还得先去森罗协会登记,见习水手证是必需的。
杜尔米耸了耸肩,就说:“确实忘了。那我们再去一趟吧。”
其实他没忘,但肯忘了的时候,他也故意没有提醒。因为他想再去看看邓莫尔船长的情况——恰巧,黄昏就要到了。
朱利安·邓莫尔看起来一切正常,但唯独不正常的是,他遗忘了奈特一家。
的确有合理的原因能解释这个问题,比如说,朱利安不想在外人面前表现出他认识杜尔米;也或许,朱利安就是忘了杜尔米,他并不念旧,没什么更复杂的原因。
但杜尔米更想看看,朱利安的“真实面目”。
他们急匆匆又去到布莱克伍德街46号。
敲门的时候,很巧,杜尔米望见玻璃上反射的幽绿色光芒。外域重新统治了这个世界。他可怜的朋友又很倒霉地变成了一颗腐烂的鱼眼睛。
伴随着暮钟,门开了。
站在杜尔米面前的,是一具奇异的木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