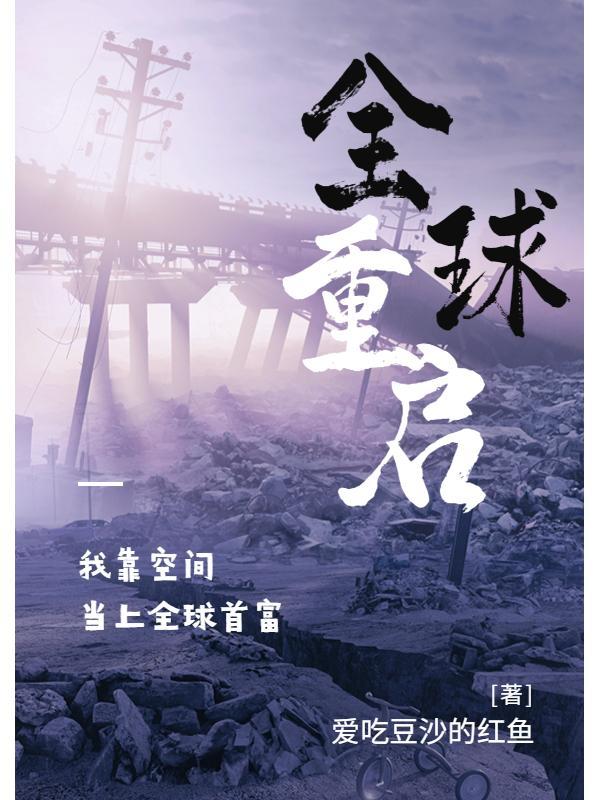笔趣小说>当官 知乎 > 第340章 回家(第1页)
第340章 回家(第1页)
冬日来的早有预料,院中的树不知不觉光了枝干,光秃秃立在那静候冬日降临,寒风拂过总爱往衣袖中钻,势要叫人切实体会凉意。
“喝药吧。”
许宴知坐在躺椅,膝上盖一层薄毯,手中握一册书卷,窗外的光洒进来将她修长的手衬得冷白,轻一开口便是白气吐出,在光映下似烟浮动,无端透出冷气。
书卷被反扣在膝上,她接过药碗凝着这卷苦涩泛起热气的黑色汤药,“还要喝多久?”
“等你的伤彻底好了就不必喝了。”
阿桃又补充一句:“是彻底好透了。”
许宴知微顿,半笑半无奈:“其实我的身子也没有这么虚弱吧?”
阿桃哼哼两声,“是不虚弱,但为了什么喝药你自己心里清楚。”
许宴知一抬眉,自认理亏,将药一饮而尽。
阿桃见状将一碟果脯递过去。
许宴知推开她的手,“不必了,撤下去吧。”
阿桃没吭声,将果脯不由分说的塞进她手里便端着药碗出去了。
许宴知端着一小碟果脯淡淡失笑,她依靠着躺椅望向窗外,捏起果脯送入口中,甜滋滋的,瞬间冲淡了口中苦涩。
她一个一个将果脯吃完,口中甜到腻,这样松闲的午后足以勾起人的困欲,她有些顾不上口中的甜腻,懒懒倚着不想动弹。
也是冬日,入眼是覆满的白。
云清学宫积了厚厚的雪,整个学宫隐在白茫茫之下更显沉静巍峨。
许宴知闲不住,去后山捉了兔子烤来吃,觉得滋味不够又怂恿着何元去偷虚清酿的酒,何元叫上宋雪把风,抱了一坛子的酒给许宴知。
三人分喝了一整坛酒,何元醉醺醺时才后知后觉担心会被虚清责骂,说什么也要亲自去找虚清认错,宋雪拦着不让,“你去认错那我和师姐怎么办?”
二人拉拉扯扯争执不休,许宴知也醉得厉害,杵着下巴盯着他二人傻乐,待他二人吵累了回过神来才觉许宴知没了踪影。
于是他二人酒劲未过就满学宫去寻许宴知,跑了一遭下来满学宫的人都知道他二人喝了酒。
顾月笙一手拎一个醉鬼把他俩送回房,又四处去寻许宴知的踪影。
从白日寻到天黑都没见到人,顾月笙有些慌了,只能去同虚清实话实说。
虚清骂骂咧咧的让学宫的其他师兄弟一起去找许宴知,一伙人提着灯笼、举着火把在后山找了许久都没有现她的人影,虚清起初还骂个不停,找到最后也不骂了,面色愈沉重。
在后山没找到人,虚清又带着人回学宫找,走到学宫门口时顾月笙眼尖瞥见大门一旁的石雕旁缩着个人,走过去一瞧,果然是许宴知。
她怀里抱着酒坛子,靠在石雕旁睡着了。
虚清松了口气,又立马气得胡须乱颤,他抬起腿作势要把她踢醒,可临了还是没舍得踢,轻轻一捏她的脸,“小崽子,别在这睡,起来了。”
许宴知被叫醒,一见是虚清便笑嘻嘻的,她从空了的酒坛中提起一只野兔,“老头,给你做兔毛手暖。”
虚清哭笑不得,“你出去就是为了这个?”
许宴知答非所问:“我特意抓的这只兔子,皮毛好,给你做手暖正好。”
虚清拍拍她肩上浮雪,“怎么喝这么多酒?”
“我没醉。”
虚清瞧着她脸红扑扑的:“……”
“行了,回去吧,等你酒醒了再收拾你。”
许宴知醉了酒,听话又不听话。
虚清哄她回房休息,她口中答应却坐在地上抱着虚清的一条腿说什么也不起来,“老头,师父,老头,”她顿了顿,“老头老头老头老头!”
虚清弹一下她额头,“做什么?”
“我给你养老吧。”
虚清一滞,眼眶不由湿润,正欣慰感动时又听她说:“然后你养的鸡和酿的酒就都归我了,我全给你吃了。”
“好徒——好个混账东西。”
许宴知充耳不闻,紧抱着虚清的腿用脸蹭了蹭,“老头,真羡慕你。”
“羡慕什么?”
“羡慕你有我这么个好徒儿。”
“……”
虚清忍无可忍,拎着许宴知后衣领把她从地上提溜起来,“滚回自己的房间去。”
“老头,我是不是你最喜欢的徒儿?”
“不是。”
“是吧?是吧?”
“都说了不是!”
“你果然最喜欢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