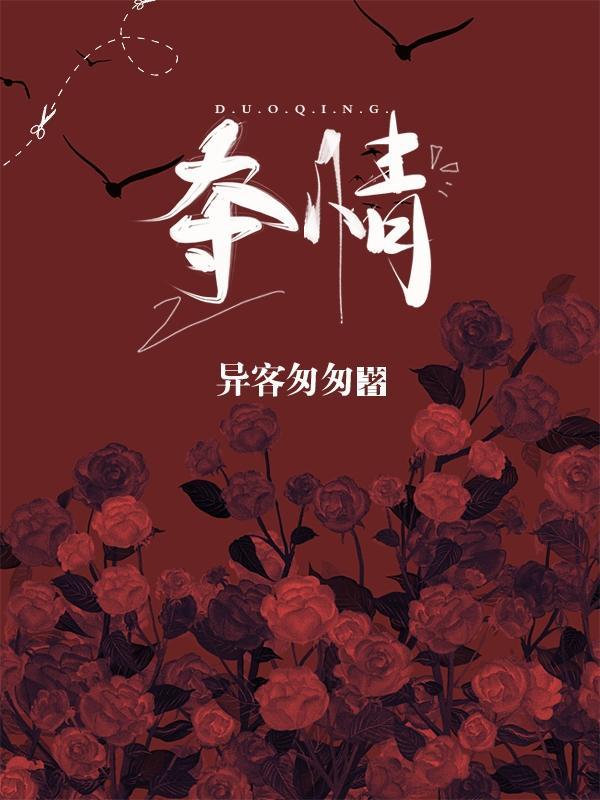笔趣小说>农夫家的漂亮小人鱼 作者山山尔 > 第46頁(第2页)
第46頁(第2页)
江飲冬:「我總不能任那癩子在我頭上拉糞還無動於衷,讓旁人白白看了笑話吧?」
江立誠:「……」
他瞥了瞥江飲冬手裡的餅子,幽幽道:「你還吃不吃飯了?」
江飲冬:「……」
好在因此江立誠也止了話頭,兩人匆匆吃罷飯。
江立誠的本想說他如今家裡養這個不明不白的人,倒不如原先的紀寧,好歹是風評好的哥兒,有漢子追也沒得說。
誰知那寧哥兒也不是個老實安穩的,江飲冬都看上個啥些人吶。
江立誠一個大老爺們,對人家哥兒的事不好打聽,眼下侄子和他屋裡那個無名無分,他也不好上門對人家指指點點。
只是他這侄子是個莽漢,竟然拿斧頭不要命護著的。
這般架勢比對寧哥兒都厲害,簡直是被妖精糊了眼。萬一將來出了什麼岔子,後悔可晚了。
誰曉得他大侄子還是個風流痴情種!
「叔就想得個準話,那哥兒姓甚名誰,家人在何處,到底是清白人家還是翠樓那地方來的?」叔侄倆坐在廊檐下,江立誠搖著蒲扇問。
最後一句問的心虛,清白哥兒怎會孤男寡哥兒和冬子住同一間屋子,還住了十天半個月。
按照那紀寧的架勢,都得給孩子準備衣裳了。
「叔,你要的可不止一個準話。」江飲冬摸了摸鼻子,除了名字,他對魏魚還真的一無所知。
除了他零星透露出從前和別人一塊生活過,瞧著不像有什麼人魚家人的樣,分明就是個長了尾巴的普通男人。
普通漂亮男人。
但有一點是確定的。
「清白,絕對的清白,就跟你扇出來的清風一般。」
江飲冬蹭他二叔扇的涼風。
一個男人能講究個什麼清不清白,何況魏魚尚未娶妻,還是個雛兒魚。
「江月不都去看過了,人家因為腿傷才住我那兒,走不得道,不是我故意把人圈屋裡。」
「小月把那哥兒吹的天花亂墜,說那寧哥兒都被你攆走了。」江立誠想到了什麼,臉一沉,「你還想蒙二叔,他還跟我說你倆睡一個床。」
江飲冬:「……沒,我打地鋪。」
江飲冬見江月在灶房門邊露個腦袋,聽見她爹的話朝他笑,嘴咧的跟塊西瓜瓤似的。
「無論你和那哥兒是什麼關係,往後成不成親,他都不能繼續住你那。」江立誠板起臉,嚴肅道,「他若是清白哥兒那更不行。別悶不吭聲弄出個孩子出來,讓人沒臉。」
江飲冬嗤笑,「我能幹那種事?」
以前沒幹過,眼下更沒得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