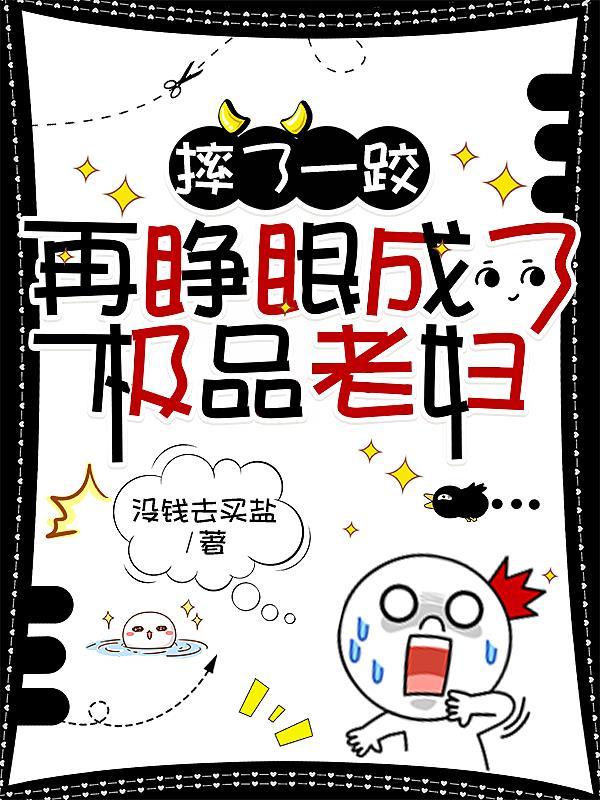笔趣小说>群魔主角 > 第50页(第1页)
第50页(第1页)
施更生站起来朝两个人挥手,三个人会合后,谢禹看见坐在一边等的司机,就问:“还有事?”
“谢先生半个小时前打电话过来,说晚上风浪大,怕是不好回去,问阿禹少爷是不是就在岛上住一晚,避一避风。”
谢家在纪安岛也有房子,而司机刚才说的话谢禹早在去看电影之前就想到了。他看看施更生和陈楷,反去问他们:“你们说呢。”
施更生至今没有从晕船的噩梦中恢复,又在过来的路上看到浪的势头,想到还要坐船回去,脸早就白了。如今听说今晚能在岛上住一个晚上,忙不迭地点头:“我没意见。其实我本来想说,如果可以的话,今晚我宁可在这里住一个晚上,等天亮了风小一点再搭渡船回去……”
谢禹点头,表示听见了:“那陈楷你呢?”
陈楷也表示没意见:“我都可以。”
“那好,那我们先去吃晚饭吧。”
最初的打算是只住一晚,但第二天天气并没有好转,风势反而有变本加厉的趋势,等到第三天第四天依然如此,谢禹就知道他们被困在岛上了。
他也不知道这是不是算得上天遂人愿,但纪安岛上的生活素来是安逸的:房子很大,踞在岛的的高处,各个房间都看得见海,又有下人常年守着,一点也不乏人气;邓碧宁不喜欢谢辰喝酒,谢辰就把自己买的别人送的好酒统统藏在岛上的房子里,现在谢禹既然住在这里,酒窖就成了每天晚上必去的地方,就连去外面吃饭也不忘记带上一瓶走;谢禹决定提早休假,也给同样无法离开的施更生和陈楷放假,没人工作,也不提工作,除了出去吃饭和散步,谢禹会上那家以回播老电影知名的电影院、施更生自得其乐地逛街、陈楷就窝在书店或者去围着岛长跑,然后谢禹发现,原来被天气羁留在岛上的熟人,远远比想像得多……
既然在放假,那么打牌简直是理所当然的。谢禹以前读书的时候学过各种花样的牌的玩法,如今趁着好天时地利一一重温,教陈楷和施更生打,也约同样留在岛上的朋友过来玩,也不管手是不是不方便,往往打到下半夜还意犹未尽。施更生有一次输得狠了,换了四五种玩法都没翻身,又借着一点酒意,惊呼:“谢禹先生,原来你这么能玩牌的,真是真人不露相”,谢禹起先还很平静地说“哦,没听说过那句话吗,只有牌桌上是不能旁人代劳的”,但听到这句话陈楷也笑眯眯地看着他,谢禹也被他们看得不得以地别开脸,灯光下酒瓶和郁金香杯熠熠生辉。
滞留在纪安岛的第六天,天气忽然放晴了,风也转小了一些,他们吃完晚饭早早回来,也没有打牌——圣诞节快要到了,去的餐厅正好有一个小型舞会,陈楷看着看着随口说不会跳舞,把施更生乐得不行,连声说要教他,于是回去之后谢禹让家里的下人找来唱片,看施更生兴致勃勃地教陈楷跳舞。
这房子里留下来的唱片还是谢禹母亲的藏品,自然都是老歌,女歌手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唱出爵士调,懒洋洋的拍子最适合初学者。
他们还穿着晚餐时候的衣服,陈楷把外衣脱了,单穿一件衬衣,和一袭黛色裙子的施更生站在一起,甚是赏心悦目。他平日里素来是手脚灵活的年轻人,但眼下搂住娇小的施更生,随着她的指挥踩步转圈,竟然也显得有些手忙脚乱的笨拙了。
半张唱片放完,陈楷依然是明显手脚不协调地不停踩施更生的脚,又时不时和忍不住笑场的施更生一起笑闹作一团。谢禹在一旁静静看了半天,看陈楷逐步入神无暇他顾,这才一个人不做声地去了东边的阳台。
阳台上一角的矮桌上摆好了早上挑好的酒和各种口味的橄榄,谢禹坐下后扯过毯子盖住腿,借着从客厅里流出的光线开酒倒酒。天空漆黑一片,没有星星,连浅色的云层也看不见,山半腰到海边一线的人家里却闪着星星点点的灯光,天和地就像在一瞬间颠倒了过来。
他看得入了神,直到脚步声近在身边才意识过来。陈楷的声音里满是笑意:“跳舞太难了,我觉得我不笨啊,怎么一动脚就像大象跳芭蕾呢……唉,你怎么一声不吭躲到这里了。”
酒入腹之后心胃都是暖的,只是在冷风里坐久了,手和脸都像是没什么知觉了。谢禹靠在椅子上,半天才接过话,声音也被风吹哑了:“……嗯,坐吧,别问我,我没跳过舞。”
“……啊,好。”陈楷乍听起来有些不知所措,还是慢慢坐在了矮桌另一侧的那张椅子上。谢禹扭过头去打量他,慢慢问:“喝什么?”
桌子上的三瓶酒都开了,六个杯子里深浅不一的都是酒,陈楷随手拿起一杯,浅浅抿了一口:“我不喜欢这个味道。”
“你喜欢什么?”
他想了想:“昨晚那种挺好喝的。”
谢禹从桌子底下摸起一个空杯子,又倒了一杯给他推过去:“喝喝看。”
陈楷先是谨慎地喝了一小口,又一气喝光了:“这个不错。”
“和昨晚的一个牌子,差两年。”谢禹淡淡地说,想起的却是若干年前的夏天,他躺在河边的草坪上,看同伴在河水里嬉戏,水流下的身体如同一条皎白而敏捷的鱼。那时橘科植物开始结实,空气里若隐若现的柑橘香调。餐布上林立着各色酒瓶子,空酒杯横七竖八,半口残酒在杯底荡来荡去,仿佛被晕染开的玫瑰色颜料。那里的夏天白昼格外长,九十点钟天空才暗下去,暮色里天空尽头泛着淡淡的橙黄色和蓝紫色,又被飞机拖过一道道看不到尽头的白线,仿佛未完成又再圆满不过的画布。
“以前,那是很早以前了,我们老是去河边,就像现在这样,挑上七八瓶不同年份不同国家的酒,他先下水我在树底下看书,等到都累了,就躺下来喝酒。一开始还一种种仔细喝,自欺欺人说是在学品酒。后来都喝乱了,混起来喝,喝醉了闭上眼就睡,睡起来,晚上十点天还没有黑透……”过了好一会儿谢禹才意识到这个放松慵懒的低沉声音是自己的,他暗暗笑了一下,还是说下去了,“不说也罢。哦,你不是问我为什么一定要写陆维止的书,其实不在于写不写,但是如果一些资料现在不留下来,等这些人死了,空白就更多了……”
陈楷突兀地打断他,问了一句完全不相干的:“‘你们’,是谁?”
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不由自主地手肘搭上了桌子,上半身朝着谢禹这边倚过来几分;于是酒味也跟着飘过来。
只喝了一杯。谢禹暗自苦笑。陈楷的脸并不分明,被无数深浅不一的阴影掩盖了,又随着他歪歪斜斜越靠越近,那些阴影一层层被温柔地拨开,最先看清楚的是眉毛,然后眼睛,脸颊,再到鼻梁,谢禹注视着他半合的嘴唇,不置可否地应:“唔?”
这下连脸颊的红光都依稀可见了,酒气薄雾般扑在谢禹的眼睛上,他的视线微妙地模糊起来,他听见陈楷顿了一顿,又重复了一遍:“你说的‘你们’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