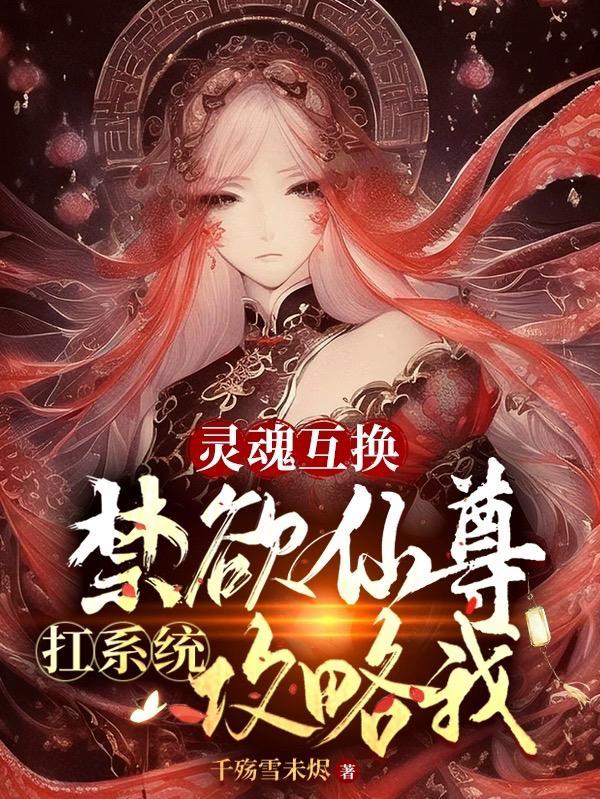笔趣小说>折骨松梢月免费 > 第49頁(第1页)
第49頁(第1页)
「便是靠近晏城那座山里,建在山谷當中。」
言罷白枝玉又忽然想起什麼,「小槿兒當真不找了麼?」
「山里夜間冷,又多有野獸,他眼瞎瞧不見路,許是早就死了,」季蕭未臉上掛著一道微不可見的冷笑,嘲弄道,「不過一個奴隸,枝玉可是太將他放在心上了些?」
白枝玉沒應聲,只是臉色有些難看。
二人轉過彎去,忽然瞧見吳信然舉著傘一人站在前頭,鞋已然有些濕了,不知站了多久。
季蕭未便也停了步子,抬指掩住唇瓣悶咳了兩聲,啞聲道:「吳御史有何事?」
「寧城災情嚴峻,信然想同陛下商議一下賑災之事,」吳信然臉上帶著毫無挑剔的笑意,轉而又輕輕「啊」了一聲,「還有便是,那殺人的惡鬼。。。。。。」
「那殺人的惡鬼,無人見過他的模樣,總是夜間出現,來無影去無蹤。」
酒樓的角落裡,幾個商戶正湊在一起悄聲說話,竊竊私語道:「什麼人都殺,誰也摸不清是為何,整個鎮上成日戰戰兢兢,無人不擔心自己突然掉腦袋。」
「指不定現在便在我們這群人當中。」
「別說得如此嚇人。」
擔心隔牆有耳,幾人便不再多說,也不敢在寧城多待,收拾東西準備離開此處。
角落處安靜坐著一個戴著帷帽的少年,身形頎長,帽檐輕紗將面龐遮擋得乾淨,只能根據身形揣測他的樣貌。
他在椅子上坐了一會兒,某個在一旁商鋪中買了胭脂的少女穿過街道,踩著水淋著雨快步跑入酒樓中,跺跺腳道:「小郎君,我們走吧。」
木朝生嗓音輕輕,含著一絲笑意,說了句「好」。
少女便攙著他站起來,慢吞吞往外走。
寧城一如晏城,驟雨不歇,綿延下了許多日,木朝生身上還有傷,總覺得潮冷,身體很不舒服,連帶著心情也有些不太爽利。
少女性子大大咧咧,隔著帷帽也不曾察覺他的情緒變動,只將傘撐開舉起擋在木朝生頭頂,道:「近幾日多雨,花街人都少了許多,你這段時間也能稍稍清閒些。」
木朝生輕輕「嗯」了一聲。
「也不知道是否還與近幾日死人的事情有關,說來也奇怪,花街到現在還沒出現過這般情況呢。」
「講起來不太吉利,」木朝生好意提醒她,「往後別再說這樣的話了。」
「好哦。」
他們沿著街道往花街走,街上行人少了大半,只有匆匆幾個路人。
悶雷自天際響起,雨珠淅淅瀝瀝落下來,拍打在傘面上,又自傘沿不斷滴落,砸在地面之上。
少女攙著木朝生行過漫長街道,直到在花街街口轉過彎去,再也瞧不見人影,並未注意到身後與之擦肩而過的、靜默佇立在雨中的那個撐著傘的男人。
作者有話說:
本文又名《季蕭未丟狗紀事》,木木溜了快活了快半個月,馬上就要被抓回去打pp
周二請個假拉一下千字QaQ,周四見啦~
第25章瘋長的欲望
木朝生這近半月都在花街暫住,隱姓埋名,遮掩自己的眼睛,只同外人說自己短視,視物不清。
那人牙子將他賣到花街,轉眼錢財都落到自己手上。
在花街這段時日除了砍兩隻手,殺兩個人,倒也沒別的什麼大事。
木朝生本打算物色一個來尋花問柳的官員,控制對方將自己帶走,之後再借用官府的錢財離開寧城,但那些官員除了占人便宜半分用處都不曾有,木朝生將其殺了,又因為眼盲不便處理屍體,只能將其草率地埋在城外的樹叢中,或是卡在樹幹里。
等寧城雨季到來,驟雨之下那些屍體便再也藏不住,一時間引起了寧城眾人的恐慌。
木朝生生得漂亮,再加上有意引導,在花街上小有名氣。
沒幾天便哄著老鴇給自己安置了一間舒適的屋子,還給他安排了貼身伺候的侍女。
只是這侍女年歲不大,活潑又多言,木朝生聽著她在一旁八卦,忽然說起寧城的災情,山中許多村落突遭水災,皇帝似乎要親自來此賑災以定民心。
木朝生摁著眉心的手忽地頓了頓,驀地直起身來。
季蕭未若是要到寧城,這寧城地界窄小,豈不是很容易便會被發現。
看來實在不能久留。
他的催眠之術可使用的效用很低,很容易便會失效,否則當時也不會匆促將人牙子殺了扔在山裡,本打算再等一等,現在時間已然不夠,等不住了。
今夜必須想辦法離開花街,明後日就要啟程離開寧城。
木朝生咬咬唇瓣,起身摸索出了門,叫侍女到前廳將自己的牌子掛上。
他給自己隨便起了個名字,十分老土,名叫春花,起初無人看得上這樸素的名字,木朝生也樂得無人打擾,成日在廂房消磨時光。
直到某日有個官員喝醉酒去小解,回到花街時走錯了屋子,瞧見了木朝生的面容,這才將春花這個名字推了出去。
那官員那日被木朝生從樓上推下去,摔斷了腿,已有許多日不曾來,今夜倒是找了機會上花街尋歡,一來便點名要見春花。
木朝生原以為自己已經做好了準備,等對方的手摸到自己的手背時才知道是自己想得太簡單。
他還是很討厭這樣帶著欲望的不堪接觸,無論從前在陳王腳邊怎樣隱忍蟄伏,始終還是討厭、不適應、永遠不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