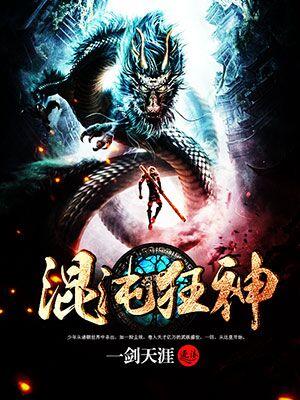笔趣小说>红楼梦迎春原文 > 绣橘(第2页)
绣橘(第2页)
未经思索,迎春便问了一句。
不待绣橘说话,迎春自己便怔住了。
她已决定再不如上一世一般随遇而安,且同父母请安,本就是名正言顺的事情,怎能因着贾母和王夫人退缩呢!若是这般瞻前顾后,自己便是知道那些后事又能如何,不过是将前世种种再经历一遍罢了,难道便能甘心不成!
想得通了,迎春抬头看着绣橘,坚定道:“这雪也停了,若父亲母亲有空,明日咱们便过去问个安罢。”
看着绣橘瞬间亮起来的眸子,迎春将旁边的丝线拿过来,示意她开始批线。她自己则拿起桌上的花样子在手里,“这几日天冷,咱们赶紧做个袖笼,老爷出门也暖和些。”
“嗳。”
绣橘忙答应一声,低下头去分线,嘴角却翘了又翘。
冬月里天寒,不当差的都窝在屋子里猫冬,并无人顶着凌冽的寒风在外逗留。贾府并非刻薄人家,并不因此责难下面的人,因而总是比往常静一些。
这会子,房门一关,外面只偶有风扑在窗棱上的声音。
迎春靠在熏笼上,手里的针上下翻飞,蜜合色的料子上渐渐显出竹青的暗纹,到底是选了竹枝纹的花样!
绣橘自各色丝线中抬起头,见迎春绣的认真,不由得抿唇。
她确实是贾赦做主送过来的!
她爹田平自小便跟着贾赦,乃是贾赦心腹,替贾赦管着下面的庄子,也是东院得脸的管事。
只是他常年去小面的庄子上巡视,总是不在家的时候多。她妈又在东院的灶上当差,也不常回来。
她年岁小,一个人在家中爹妈总是不放心,才求了老爷,送到姑娘身边伺候。
可她比姑娘年岁还小一些,姑娘哪里用她伺候呢,不过是将她当做玩伴罢了。
但她记得她爹说大房不易,委屈了姑娘,她虽不明就里,却也将话听到了心里。
说起来,如今荣府虽是二房当家,但迎春养在贾母房里,她又是姑娘,尽管比不上宝玉,对府中下人来说,却也是极好的去处了。
贾府以诗书礼仪传家,自是没有争抢攀比,打骂下人等小家子气的行事。
府中的姑娘们,二姑娘宽厚温和,三姑娘精明厉害,四姑娘还小,宝玉又是一心只有姐妹的,便是后来有了林姑娘,也从未有什么矛盾。
大家一处起居上学,吃穿用度俱是一般无二。虽性格各异,各有擅长,却厮抬厮敬,相处的十分融洽。
尤其二姑娘最是个没脾气的,姑娘们不在一处时,不过一盏茶,或是打棋谱,或是看书,或是串珠赏花,她自己便能自在半晌,最是好伺候。
王嬷嬷虽对下面严厉,却是个直的,见她能时常逗得姑娘开心,对她陪着姑娘做耍之事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只是年岁渐长,她渐渐觉得有哪里不对。
想不出所以然,她便回去寻了她爹。
田平先是问她,“可是姑娘叫你来的?”
见她摇头,她爹便叹息着揉了揉她的头发,言说只要伺候好姑娘便是,莫要想的太多。
她虽应了下来,心里却没有真正将此事放下。
还是有一日同司棋说话,司琪抱怨她老娘非要她多同姑娘说些太太的好处,她才猛然意识到:姑娘是大房的姑娘,虽说养在这边,却如何能真正同三姑娘一般行事呢!
她细细问了司棋,司棋却道,太太已经将她予了姑娘,她自是处处以姑娘的意思为重。姑娘觉得在这边更自在些,她便不愿逆着来。
她说:“你也不是不知道府里的情况。姑娘不过能松快几年,何苦再逼她。”
绣橘看着她,张张嘴,想说什么却又没有说出来。她想起父亲的话,想来父亲也是这样的意思吧!
不!或许是老爷的意思呢!
……
不过,如今可是姑娘自己想通了呢!
丝线一圈一圈的绕在浮雕梅花白玉板上,玉色莹润,更显得丝线鲜艳。莫名的,绣橘便觉得雀跃起来。她抬头看看外面的天色,将最后的线头卡住,起身唤了外面守着的小丫头子。
再回转进来,身后便跟了两个婆子。
将榻上的小炕桌放下来,另一个则麻利的打开食盒,将饭菜摆好便退了出去,只说一会子过来收拾。
绣橘这才看着她们另倒了水,伺候迎春洗了手,才服侍着用饭。
她先舀了一碗酸笋鸡皮汤在碗里递给迎春:“这几日天冷,炭火用的足了些,姑娘且先喝口汤开开胃。”
迎春接过喝了一口,笑着看她,“这会子就咱们自己,你也不用拘着了,一同吃吧。”
绣橘答应一声,便在脚踏上斜欠着身子坐了,自己端了饭在手里。
府里主子们厚道,赏饭赐菜不是什么稀奇事。但也只有主子们贴身伺候的,才能在无人处松快一些。
二人静静吃完,绣橘便奉了茶来,迎春接在手里捧着,觑着她道:“可是嬷嬷单给你发月钱了?”
啊?
绣橘有些费解的抬头,见迎春正挂着戏谑的笑意看着自己,便红了脸,“人家替姑娘急,姑娘竟打趣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