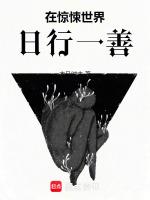笔趣小说>江山聘你 窃腰 > 第七十三章 第七十三章(第1页)
第七十三章 第七十三章(第1页)
「你……」究竟是齊曕,還是賀泠?
話到了嘴邊,不知為何,姜嬈卻問不出口了。
彷彿有一種近鄉情怯的感覺在作祟,一開口,將她原本想問的話變成了旁的:「你……你為何選擇服用毒藥誘騙孟家……侯爺大可以告知我真相,我可以陪侯爺一起演戲,不用服毒藥的……」
齊曕怔了下。
他沒想到姜嬈要問的是這個,深看了她一眼。
片刻,他眼底的掙扎和猶豫漸漸沉寂下去,只落寞地牽了下嘴角:「當時你正打算離開,我想如果我病得很重的話,你會不會心軟留下來。」
齊曕伸手,大掌將姜嬈的小手包裹進手心,笑容明銳起來,彷彿剛剛的落寞只是錯覺:「事實證明,嬈嬈還是心疼我的。」
他話音含著笑,姜嬈沒看他,只低頭,看著兩人交纏在一起的手指,沒說話。
齊曕察覺她情緒低落,卻不知為何,只好轉了話題,逗弄她道:「臣還記得,臣病著的時候,公主似乎還因為某件事吃醋了?」
姜嬈一下子反應過來,猛地抬眼看他,心虛使得她下意識反駁:「什、什麼醋……沒有的事!」
姜嬈趁機立馬將手抽出來,剛要起身——
未等她睜眼,男人沉穩的話音落進她頸窩:「睡吧,今夜換臣守著公主。」
身體有些緊繃,她以為他會繼續,可他卻退開了。
榻上倚坐著的人忽然咳嗽起來。
「咳咳……」
一想到他的身份,她身體裡的血液就一忽兒熱,一忽兒涼,兩種情緒如同水火,此消彼長,誰也不肯讓。
齊曕眉眼輕彎,寵溺笑起來:「好好好,公主說沒有就沒有。」
細嫩的肌膚只是被攥著蹭了蹭,立馬浮現一片紅,齊曕怕弄疼她,手稍稍鬆了幾分。
而這一晚,是她頭一回在齊曕身邊睡得不安穩。
話是這麼說,揶揄的笑意卻未減,姜嬈被笑得羞赧,要將被齊曕牽著的手抽走,他立馬攥緊,她便用力掙脫。
姜嬈一時怔然,那張俊逸的臉就在她眼前慢慢放大,她沒躲,本能地閉上了眼睛。
她在這世上已經沒有親人,人一旦一無所有,再回想起過去的圓滿,就會覺得彷彿只是美好的幻境。時間越久,那不真實的感覺就越強烈,到最後,她甚至懷疑過去的一切根本都是假的。
「侯爺不是……沒力氣嗎……」明明方才喝粥都是她餵的。
「現在有了。」齊曕淡道,低沉的嗓音聽起來有種別樣的晦暗,像是某種蟄伏的獸類發起進攻前壓抑的低鳴。
姜嬈兀自靜止了片刻,到底還是什麼話都沒說,就這麼在他懷裡睡了。
齊曕昏睡這些時日,她照顧他幾乎已經成了本能,這會兒冷不丁聽見他咳嗽,下意識地就連忙探身湊過去,拍著他給他順氣。
隨即,眼睫被溫軟的唇輕輕壓了壓,微熱的鼻息落在她額前,拂過肌膚,有點癢。
眼前一陣天旋地轉,等姜嬈反應過來的時候,男人狹長含笑的桃花眼已經近在眼前。
他和她不僅有著共同的回憶,相同的經歷,更重要的是,他和她,彼此都是對對方過去美好存在過的最有溫度的證明。
她的手剛落到人身上,不想榻上的人突然一動,大掌忽地扣住她的腰,他握著她細軟腰肢一帶,竟是直接將她整個人扔到了里榻。
但如果齊曕真的是賀泠的話,那這天地之間,她就不再是孤身一人了。
他記得她嬌閨無邪,曾受萬千寵愛,天真爛漫。
她知道他少年如玉,滿腔赤子熱血,矢志不移。
如果僅僅是這樣的話,她一定會熱烈地、瘋狂地擁抱他,不顧一切地刨根問底。
可是,她和賀泠之間,不僅如此。
國破前的兩年,上殷大旱,許多地方的百姓辛苦耕種一季,最後卻顆粒無收。
與此同時,上殷得到消息,晉國正在大舉屯兵練武,似乎在做戰事前的準備。
晉國虎視眈眈,雖不知道其目的究竟是上殷還是漳國,但所謂居安思危,按理說,上殷應該早做防範。
賀氏、蕭氏、穆氏,三氏得到消息後,聯合進宮,提議徵兵買馬,以應備戰需。
可那時候正逢舉國遭受旱災,擴軍練兵、戰馬鎧甲,哪一樣不要銀子?因為賑災,國庫里的銀子已經撥出去不少,就算剩下的全拿出來充作軍資,也遠遠不夠。
如果真要屯兵秣馬,那就只能加收賦稅了。
可是,剛經歷大旱,剛撥了賑災銀,一轉眼就加收賦稅,且不說這樣會不會叫百姓覺得朝廷朝令夕改,就單單說百姓,此時加收賦稅,無異於用百姓的血去養兵養戰。
那時候的姜嬈還不懂父皇在苦惱什麼,只記得他很長一段時間裡都愁眉不展。
父皇仁政愛民,最後還是駁回了賀蕭穆三氏所請。
蕭家和穆家見擰不過帝王心意,失望之下也只能作罷,唯有賀家,賀泠的父親在父皇殿外,跪了三天三夜。
然而直到他最後暈倒,父皇也沒同意他所請。
怎麼能不失望呢?尤其是,後來面臨那樣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