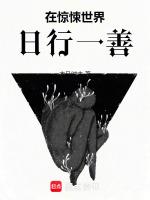笔趣小说>江山聘你窃腰全文免费阅读 > 第六十八章 第六十八章(第1页)
第六十八章 第六十八章(第1页)
馮邑聞言抬眼看姜嬈,臉上並未有什麼意外的神色,他十分坦誠地點點頭:「是,侯爺的確是染了瘟疫。」
看到街上那些醫館前的一條條長隊,姜嬈心裡就已經大致確定了,此刻也沒什麼好驚慌的,只又問:「你可能研製出治好這瘟疫的解藥?」
馮邑猶豫了一瞬,終是點頭:「能。」
姜嬈剛鬆了口氣,馮邑續道:「只不過在下需要時間。但公主放心,在下已經給侯爺用了葯,侯爺暫時不會有性命之憂。」
姜嬈神色略沉了沉。
在這暗潮湧動的安梁城,沒有行動能力,一旦城裡生亂,齊曕身居高位又毫無反抗之力,其實與死了也沒什麼兩樣。
兩日後。瘟疫爆發。
安梁封了城,姜嬈無比慶幸姜琸走得早,不然困在城裡,只怕凶多吉少。
安梁城內,所有人都被勒令不得出門,姜嬈求之不得,立馬叫人關了侯府大門還上了鎖,除了必要的採買,幾乎所有人都閉門不出。而就連採買,每次回來的人都會先被隔離,確認沒有染上瘟疫,才會將採買的東西發放,將人放出來。是以採買這事,總要好幾撥人輪流著去辦。
「咳……水……」床榻上,忽然傳來一聲極低微的呢喃。
馮邑見姜嬈低著頭不知在想什麼,沒說話,又對她道:「在下多嘴問一句,公主照顧侯爺,夜間可是同榻?」
雖然那時候,她以為齊曕只是染了風寒,以為有馮邑在,齊曕要不了兩日就會好轉痊癒。
姜嬈抬起頭,收回思緒,隔著屏風看了裡間一眼道:「不是同榻,裡間有張榻椅,我睡在榻椅上。」
既然馮邑已經來了,原本是每日午後叫他給齊曕問脈,索性姜嬈就叫他一併給齊曕看了。
姜嬈的眉頭這才鬆開,然而轉念一想,她又低下頭去,很是自責——她因答應了姜琸和他一起離開安梁,竟真的就丟下了病中的齊曕,險些一走了之。
馮邑點點頭,又囑咐了一句:「這就好,侯爺到底是染了瘟疫,公主切莫和侯爺過於親熱。」
姜嬈睡得淺,只是閉著眼,立馬就聽見了這聲音,她一骨碌爬起來,立馬去齊曕榻邊,從小几上倒了水放在手邊,又攙扶起榻上的人,端水餵給他慢慢地喝下。
姜嬈微微蹙著的眉頭並沒有舒展,她不解道:「但是昨日夜裡侯爺醒了一回,說是口渴,我給餵了水,侯爺這麼忽然醒過來,應當是好事吧?」
入夜。萬籟無聲。
馮邑沉吟片刻,道:「這是正常情況,侯爺只是昏睡,並非昏迷不醒,若渴了,公主儘管餵水就是。」
看完,馮邑道:「侯爺的情況還算穩定,沒有大礙,公主放心。」
明明只是一點極微弱的月色,姜嬈躺在榻椅上,睡意卻被照得盡消,她有些睡不安穩,翻來覆去的,動作倒是很輕,生怕吵了齊曕休息。
府里各處都灑了石灰,熏了艾草,姜嬈聞不習慣這味道,出屋子的時候被嗆得一連咳嗽了好幾聲,登時嚇得拂冬慌了神,飛跑著就去妙安院將馮邑拽來了竹苑,給姜嬈看診。
月偏移,長夜已不知過去多少。
馮邑沒接話,朝屏風後深看了一眼,像是欲言又止,最終卻也沒說什麼,離開了竹苑。
馮邑又沉默了片刻,終於點了點頭:「侯爺喝了葯,大約是藥性壓制住了疫症,所以有所好轉。」
月華靜靜流淌,漏過窗柩輕灑進室內,褪去冷意,連暈光都變得微薄。
姜嬈一陣苦笑:「別說我如今沒這樣的心思,侯爺也沒這個力氣不是嗎?」
萬幸,姜嬈真的只是被嗆到了。
「可是……」姜嬈偏了偏腦袋,還是有些想不通,「之前侯爺不是昏迷了嗎,如今從昏迷變成了昏睡,有了一點模糊的意識,應當是有所好轉吧?」
這一套動作她做的十分熟練,等齊曕喝完,她放下盞杯,再將人扶著重躺下。
然而,她剛要扶齊曕躺下,腰間忽然落下一掌溫熱。
熟悉的溫度,掌心有一層薄繭,挲得人發癢。
姜嬈身體一僵,等反應過來是齊曕抱她了,她話音里漫上掩不住的欣喜:「侯爺!你醒了?!」
卻無人回答。
病中無力,齊曕似是撐不住自己的身體,頭一點一點偏倒,慢慢靠落在姜嬈肩頭。
他極高,同坐在榻上亦比她高出一個頭,他的腦袋倚靠過來,便深埋進了她頸窩。
呼吸噴薄在頸間,少了曾經纏綿的灼熱,不知是不是齊曕過於虛弱的原因,姜嬈甚至覺得,他的呼吸帶了一絲若有若無的涼意。
她驀地覺得有些冷,心下也止不住地難過起來。
深寂的夜,黑暗原本讓人恐懼,這會兒,姜嬈卻覺得讓她心安,彷彿在這樣無人的夜裡,無論她做什麼想什麼,都不會被人發現,她終於不必逃避,也不必惶恐不安,只消遵循自己的心。
身為公主,她是整個上殷的支撐,身為皇姐,她是姜琸的依靠,唯有身為姜嬈,她只是他的嬈嬈。
不用銅牆鐵壁,不用堅不可摧,走累了可以要抱,委屈了可以想哭就哭,彷彿她還是多年前深宮高牆裡,那個不諳世事、有些驕縱任性的小姑娘。
姜嬈慢慢伸出手,回抱住齊曕,不敢太用力。
&1t;divnettadv"&1t;netter
&1t;netter
不知道過了多久,齊曕輕握在她腰上的手慢慢鬆開,滑落下去,似是陷入了更深的昏睡。